清代商人同業行幫組織。
商業行會的兩大類型 同一個城市中由同業結合組成的行會,是清代商業行會組織的基本形式。例如錢莊業中上海的南市錢業公所和北市錢業會館;藥業中蘇州的太和公所;佈業中廣州的南海佈行會館純儉堂,等等,都屬於這一類型。
按地域劃分幫口,是清代商業行會組織的另一結合形式。在內地中小城市,外省商人大多各按本籍組成商幫會館,,最常見的是:粵商有嶺南會館,一名南華館;閩商有天後宮;江西商幫有豫章會館,一名萬壽宮,湖南商人有禹王宮,陜商有三元廟,豫商有中州會館,等等。有些城市,外省商人往往因本籍人數較少,也有按省籍采取聯合組織的。如在廣西梧州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商人,合建有三江兩浙會館。在商業發達的城市,這類商幫行會組織內部分幫分業也比較細致。如在漢口,江西各商幫還分別建立有南城公所、撫州會館和臨江會館。同時,按地域結合的商幫行會,有的是同業組織,有的是不同行業的聯合組織。1882~1891年,據海關在十八個重要城市的不完全調查,由各省商幫按地域組成的會館、公所,以蘇州和廣州最多,次為蕪湖、上海、沙市、漢口、福州,再次為重慶、宜昌、九江、蒙自、天津、瓊州、梧州、龍川、沈陽、蓋平、牛莊。這類會館公所,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瞭維護遠離鄉土從事省際貿易的行商坐賈的切身利益,後來逐步發展成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很有影響的重要組織。如在重慶,有名的八省會館各幫首事常與當地官吏共同參預地方稅務等公共事務。
在同一城市裡,這兩類商業行會並存。海關的調查資料表明,上海除瞭十六個商幫會館外,有二十五個同業公所。重慶既有八個屬於省籍的商幫會館,又有十二個同業公所。梧州既有按商幫籍貫組成的三個會館,又有按行業組成的十個同業行會。在同一城市裡,商業行會采取不同的組織形式,固然反映瞭商業資本在營運上分工的發達,同時也是行會商人為瞭爭奪商業利潤,對市場分割直接造成的後果。
商業行會的職能 行會主要通過行規的強制性作用,從流通環節上調劑商品的買賣,限制彼此的自由競爭。
為瞭控制當地市場的交易,行會竭力限制外來商販;有些中介商的行會對外來客商販運到埠的大宗商貨,不許有關同業“私買私賣”,必須投行入店發賣。同時,為排除內部的競爭,行會通常采取制定度量衡標準,並由行會共同校準,不許同業私自增減輕重出入;劃一貨價銀碼,隻能由行會定期公議,酌量增減價目。此外,還規定結帳(收交)日期及抽取行用標準的限制,以及對幫夥(客師)學徒和主雇關系的種種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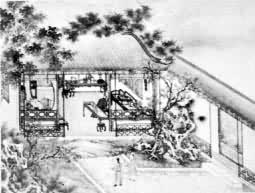 蘇州秦晉會館
蘇州秦晉會館
各業商幫行會固然多以成文的行規體現它的強制性,但是有的行會,如汕頭的漳潮會館,名曰“萬年豐”,外人稱之為汕頭公所,買賣行規一般多不見諸明文,與同幫商人之間達成的默契和交易慣例,同公佈的規章有同等約束力。盡管清代各業行會在某些方面有不少差異,但各業商幫行會所議定的行規內容所反映的強制作用大多基本相同,這就明顯地表現瞭行會職能具有一致性的特點。
商業行會與官府、外商的關系 太平天國失敗後的三十年間,行會經歷一個恢復重建的階段。商業行會與官府依然保持相互為用的關系:①官府利用行會組織包辦厘捐(即厘金),負責認捐包繳,然後由各業行會按所定厘捐核額向同行攤征,或按各行店營業額分別認繳,定期收解厘捐局,保證瞭封建政府財政稅收的穩定。行會並從中取得各種特權,進一步擴大瞭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力,對有關本行業的買賣經營的控制愈益加強。如上海的浙湖縐業公所甚至因此造成瞭對湖縐營運的壟斷。②官府利用行會組織承差,恢復官署的修建鋪設和城市的公共工程。承差是封建官府對民間工商業者進行徭役剝削的一種方式。有關商業行會也有供應差物差貨的義務。由於官府經常給價不足或根本不給,往往須由行會“賠貼”,有的行業便有幫差錢的征收,有的行業則以入會金來“賠貼差務”。為瞭均攤差務,不少行會在公同議定的行規中又把履行差務作為一種強制性的手段,使差徭強制和行會強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各業行規中往往載有所謂“違者稟究”,意指違反行規,稟官究辦。這使行規具有同法令一樣的約束力。③官府還利用行會組織管理城市工商業者,負責“約束”,使其起著保甲稽查的作用,借以鞏固城市封建統治。在封建行會勢力和封建官府勢力之間,往往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鬥爭。例如苛重的厘捐榨取,以及稅收胥吏的額外殊求,曾在光緒年間引起天津和汕頭的商人運用公所有組織的力量,以齊行的方式進行罷市反對。
這一時期,商業行會特別是與經營進出口正常貿易有關的行業,同外國洋行商人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有著深刻的矛盾。由於洋商在華享有不平等條約賦與的特權,行會雖不可能把它從當地市場完全排斥出去,但為瞭限制洋商在買賣各方面“不遵通商章程,任意作難,格外取巧”,通常采取“訟理”或“停交”的抵制。當然這種鬥爭仍具有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即使這樣,由於各通商口岸有關商幫行會在當地市場上從內部和外部堅持瞭不懈的抵制鬥爭,1896~1897年英國有一個商會訪華團報告中證實:他們在溫和而堅決的經濟絕交的情況下,不得不屈從公所提出的要求。
同時,商業行會為瞭限制興起中的新式工業企業在市場上自由地收購生產原料和出售產品,曾從中力圖施加幹預和阻撓。這是行會商人為瞭在市場上同工業資本傢爭奪利潤或分割利潤進行鬥爭的反映。
清代後期。中國社會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演變過程,當時的行會組織亦發生變化。光緒二十九年底(1904年1月),清朝政府商部奏準仿照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傢的商會組織,頒佈《商會簡明章程》,明令各省城市舊有商業行會、公所或會館等名目組織,一律改組為商會。此後,商業行會逐步改變瞭傳統的封建性質,具有瞭資產階級組織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