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П.И.柴科夫斯基
П.И.柴科夫斯基
俄國作曲傢。
生平 1840年5月7日柴科夫斯基出生在維亞特卡省卡姆斯克-沃特金斯克附近的村莊。父親是一位礦業工程師,1848年遷遷傢至聖彼得堡。1850年,柴科夫斯基入聖彼得堡法律學校學習,並選修音樂課,從師Т.И.菲利波夫學習鋼琴。1859年從法律學校畢業,進入司法部任職,同時鉆研音樂。1861年入俄羅斯音樂協會的音樂班學習。1862年在音樂學習班的基礎上成立瞭俄國第1所高等音樂學校──聖彼得堡音樂學院(今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柴科夫斯基成為該校第1批學生,在Н.И.紮連芭指導下學習和聲與復調;在А.Γ.魯賓斯坦的指導下學習配器和作曲。由於司法部的職務與學習音樂之間的矛盾,柴科夫斯基幾經考慮,於1863年毅然辭去司法部的工作而完全獻身於音樂事業。1865年,柴科夫斯基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畢業作品為康塔塔《歡樂頌》(J.C.F.席勒詩),獲得銀牌獎。同年應Н.Γ.魯賓斯坦之邀,柴科夫斯基來到莫斯科,任教於新成立的莫斯科音樂學院,並開始瞭緊張的創作活動。約10年時間,柴科夫斯基寫下瞭許多早期名作,其中包括3部交響曲、鋼琴協奏曲、歌劇、舞劇、管弦樂序曲、室內重奏等。由於教學任務繁重,柴科夫斯基為自己不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創作而苦惱。但為瞭經濟來源,他又不得不繼續擔任教學工作。1877年7月柴科夫斯基和А.И.米柳科娃結婚。這是一個不幸的婚姻,柴科夫斯基為此極為痛苦,不久即離異。創作與教學工作的矛盾和婚姻帶來的不幸,使柴科夫斯基精神負擔沉重。1876年,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建立瞭通訊友誼,這給柴科夫斯基以極大的精神安慰。梅克夫人是一位頗有文化教養的富孀,非常喜愛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兩人在頻繁的通信中建立瞭深厚的友誼。梅克夫人從1877年開始,每年給予柴科夫斯基以優厚的經濟資助,使柴科夫斯基有可能辭去音樂學院的教職,把自已的全部精力投入創作。從1877年到他去世的10多年間,是柴科夫斯基在創作上獲得輝煌成就的時期。他的第4、第5、第6交響曲以及標題交響曲《曼弗雷德》,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瑪捷帕》、《黑桃皇後》、《伊奧蘭特》,舞劇《睡美人》、《胡桃夾子》,以及《小提琴協奏曲》、《意大利隨想曲》、《1812序曲》以及許多浪漫曲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名作。
柴科夫斯基一生中曾多次去西歐旅行,並於1891年赴美國指揮演奏自己的作品。1893年5月,柴科夫斯基接受瞭英國劍橋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10月28日在聖彼得堡親自指揮其《第六交響曲》的首次演出,11月6日由於霍亂癥逝世(另一說是因自殺而死)。
創作 柴科夫斯基生活的年代正處於沙皇專制制度腐朽沒落的時期。他熱愛祖國,關心俄國人民的命運,但他又看不到俄國社會的出路。他從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俄國政治的黑暗與腐敗,但他的政治態度卻又是保守的王朝擁護者。這種無法克服的矛盾不斷促使柴科夫斯基對祖國的前途、社會的出路、人生的意義進行深刻的思考,並把這種生活感受融化到他的創作中去。這可以說是柴科夫斯基創作上的基本思想傾向。柴科夫斯基雖不直接選取現實的政治生活、社會沖突等作為自己創作的題材,但卻通過自己對於時代悲劇性的感受,深刻揭示瞭對光明理想的追求、對生活意義的理解。
柴科夫斯基是在60年代中期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高漲時期走上創作道路的,60年代的進步社會思潮給柴科夫斯基以積極的影響。盡管他在政治觀點上是比較保守的,但他一生在思想上和美學觀點上保持瞭60年代的進步傳統。從創作基本面貌上看,柴科夫斯基的前期創作比較傾向於表現對光明、歡樂的追求和信心,而後期則更傾向於表現深刻的悲劇性。他在70年代末所寫的《第四交響曲》和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則屬於他在前後兩個時期交界時的作品。
就體裁而論,柴科夫斯基是一位涉及范圍廣泛的作曲大師。他在交響曲、歌劇、舞劇、協奏曲、音樂會序曲、室內樂以及聲樂浪漫曲等方面都留下瞭大量名作。
交響曲在柴科夫斯基作品中占突出地位。柴科夫斯基一生共寫過6部交響曲和1部標題交響曲。他的第1、第2、第3交響曲寫於70年代中期以前,均屬於前期創作。這3部交響曲體現瞭柴科夫斯基與М.И.格林卡以來俄羅斯交響音樂傳統的聯系。這3部交響曲都屬於生活風俗性和抒情性作品,在主題上往往采用民歌素材。柴科夫斯基的後3部交響曲以及《曼弗雷德》交響曲。屬於後期創作,風格上轉向深刻的心理刻劃,它們的主題思想都屬於表現主人公對幸福的渴望和阻撓幸福的“厄運”之間的矛盾沖突。f小調《第四交響曲》寫於1877~1878年,作者把此曲題獻給梅克夫人,但在總譜手稿上隻寫“獻給我的摯友”。柴科夫斯基賦予這部交響曲的序奏主題以極重要的意義,讓它貫穿整個交響曲的4個樂章,稱它為整個作品的核心,是“厄運”的象征。雖然在第1樂章中個人和厄運間發生瞭悲劇性的激烈沖突,但在末樂章中則體現瞭力圖擺脫苦悶,走向人民,從人民的歡樂中獲得對生活的信心的樂觀結局。e小調《第五交響曲》寫於1888年。在這部交響曲中也有一個代表“厄運”形象的序奏主題貫穿全曲,並且全曲的最後也是在凱旋式的尾聲中結束。b小調《第六交響曲》寫於1893年,此曲完成後,柴科夫斯基接受其弟莫傑斯特的建議,題名為《悲愴》。此曲是柴科夫斯基悲劇性交響曲創作的高峰。全曲在經過激烈的戲劇性沖突和對生活的美好憧憬之後,達到的是悲劇結局。末樂章一反交響曲的傳統佈局,用非常近似追思曲氣氛的慢板代替瞭熱烈的終曲。標題交響曲《曼弗雷德》寫於1885年,這是根據G.G.拜倫的同名詩劇而寫的交響曲,抑鬱寡歡的主人公的最後命運是充滿悲劇性的。
歌劇是柴科夫斯基創作中另一重要領域。柴科夫斯基一生共寫過11部歌劇,其中最卓越的作品是他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和《黑桃皇後》。這兩部歌劇的腳本都是根據A.C.普希金的同名作品改編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寫於1877~1878年。歌劇表現瞭塔吉雅娜、奧涅金、連斯基等幾個貴族青年由於厭倦瞭本階級的生活方式,在朦朧地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上所經歷的悲劇,表現瞭歷史的趨向。音樂以悠長、抒情的旋律,細致表現人物心理為特征。《黑桃皇後》寫於1890年,所表現的主題思想也是幸福的理想被殘酷的現實所粉碎的悲劇。音樂在刻劃人物性格、表達戲劇沖突上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見彩圖)
 俄國作曲傢П.И.柴科夫斯基
俄國作曲傢П.И.柴科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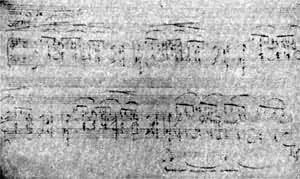 《葉甫蓋尼·奧涅金》手稿
《葉甫蓋尼·奧涅金》手稿
柴科夫斯基在舞劇音樂創作上也取得瞭具有世界意義的成就。他一生寫瞭3部舞劇音樂:《天鵝湖》(1875~1876)、《睡美人》(1888~1889)和《胡桃夾子》(1891~1892),都已成為世界舞劇藝術中影響巨大的作品,廣泛流傳在各國的芭蕾舞臺上。柴科夫斯基對舞劇音樂進行瞭許多革新,他克服瞭過去舞劇音樂的公式化弊病,賦予舞劇音樂以交響性的發展,使之更富於戲劇性,大大提高瞭舞劇音樂的表現力。
 舞劇《天鵝湖》在勃裡修劇院上演
舞劇《天鵝湖》在勃裡修劇院上演
在器樂協奏曲方面柴科夫斯基比較突出的作品是他的降b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1874~1875)和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1878)。前者是一部明朗樂觀的作品,第1樂章熱情洋溢,第2樂章優美、抒情,末樂章粗獷豪邁,並在壯麗的凱歌般的音樂中結束瞭全曲。後者也是一部充滿歡樂情緒的作品,主題音調和俄羅斯民間音樂有著內在的聯系,整個作品在質樸的風格中富於青春的朝氣和親切的抒情,並以熱烈的具有民間歌舞特點的終樂章結束全曲。
柴科夫斯基在器樂作品中還寫瞭一些著名的單章性的作品,如幻想序曲《羅密歐與朱麗葉》(1869)、《1812序曲》(1880)、《意大利隨想曲》(1880)等。《羅密歐與朱麗葉》是接受М.А.巴拉基列夫的建議而作,取材於莎士比亞原著,概括地表現瞭原著的主題思想。《1812序曲》是應魯賓斯坦之約,為莫斯科救主大教堂重建落成而作。救主大教堂於1812年毀於拿破侖入侵,故題名為《1812序曲》。這是一部以音樂描繪戰爭的通俗性樂隊作品。其中的主題多采用瞭人們較熟悉的曲調,如聖詠《上帝,拯救你的眾民》、民歌《在大門旁》以及《馬賽曲》、沙俄國歌《上帝保佑沙皇》的片斷等,分別表現戰爭雙方的形象。《意大利隨想曲》反映瞭柴科夫斯基多次旅居意大利所得到的生活感受,特別是意大利民歌所喚起的鮮明印象。
在柴科夫斯基為數不多的室內樂作品方面,以他的D大調《第一弦樂四重奏》(1871)和《a小調鋼琴三重奏》(1881~1882)最為著名。這兩部作品都顯示瞭柴科夫斯基在室內樂方面所具有的鮮明民族風格的獨創性。特別是《第一弦樂四重奏》的第2樂章“如歌的行板”,以烏克蘭民歌《瓦尼亞坐在沙發上》為主題,更是膾炙人口。大文豪Л.托爾斯泰曾被此曲感動得流淚,他說,從這個作品中可以“接觸到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a小調鋼琴三重奏》是為悼念H.Γ.魯賓斯坦而作,全曲隻有兩個樂章,但第2樂章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故全曲仍具有3個樂章的結構特點。柴科夫斯基以深沉的悼念和對往事的親切回憶來寄托對亡友的哀思。
柴科夫斯基在聲樂浪漫曲方面也寫出許多受人喜愛的珍品。他的浪漫曲風格多樣,內容廣泛,情感真摯。最突出的是那些戲劇性抒情浪漫曲,在這類浪漫曲中,也同柴科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一樣,深刻體現瞭主人公對光明幸福的渴望同黑暗現實間的激烈矛盾。如《遺忘得真快》(1870)、《在熱鬧的舞會上》(1878)、《我們曾坐在一起》(1893)、《夜》(1893)等等。
柴科夫斯基的創作深刻地反映瞭19世紀下半葉處在腐朽的沙皇專制制度下,俄國知識分子對光明的向往,對黑暗現實的苦悶壓抑的感受。他善於在矛盾沖突中捕捉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入揭示人物的內心體驗。他繼承瞭格林卡以來俄國音樂發展的成就;又註意吸取西歐音樂文化發展的經驗,重視向民間音樂學習;他把高度的專業創作技巧和俄羅斯民族音樂傳統很好地結合起來;他把清晰而感人的旋律,強烈的戲劇性沖突和濃鬱的民族風格富於獨創性地有機地融合在他的作品中,為俄國音樂文化和世界音樂文化作出瞭寶貴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