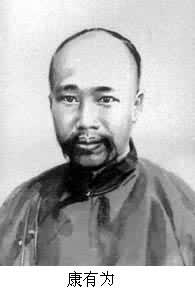 康有為
康有為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要代表,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辛亥革命前後轉變為保皇派的首領。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今廣州)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進士,授工部主事。主要著作有《新學偽經考》、《孔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日本變政考》、《大同書》、《禮運註》等。
康有為從青年時代起,就留心西學,1895年,清王朝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他憤然發起“公車上書”,反對不平等條約,呼籲救亡圖存,變法圖強,震動瞭朝野。為鼓吹變法維新,他創辦《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保國會,並繼續向清帝上書。1898年,在清光緒的支持下,康有為與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著手進行變法,但為慈禧太後、榮祿等人所反對。不久,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康有為逃亡海外。此後,他在海外組織保皇會,堅持立憲保皇,反對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從此,康有為日益落伍倒退。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出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綱領和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的政治綱領,並希冀通過爭取清王朝某些上層統治者的支持去實現。在這一過程中,他也相應地提出改革舊法律制度、采用新法的主張。他的法律思想是他的變法維新主張的組成部分,是服務於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綱領的。康有為以今文經學、儒傢“大同”思想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為其理論基礎,在“托古改制”形式下宣傳瞭某些資產階級觀點。他對中國舊的法律和制度表示不滿,並以進化論為依據,論證中國必須變法。他說:“變者,天道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尤其是在萬國並列,西方強國鷹瞵虎視的環境中,他更感到非變法不能自存,因而強調“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在“全變”的觀念下,康有為主張仿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他從實行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政體考慮,主張采用三權鼎立之制,把三權分立視為立憲精意之所在,認為隻有“三權立,然後政體備”。西方各國以行三權分立之制而強,中國則因行君主專制而弱,他指出,在三權分立之下,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統,又互相制約,君權受到限制,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君民共主。
康有為又認為建立議院以行使立法權,是實行三權分立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公車上書》、《上清帝第四書》、《上清帝第六書》及《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等奏稿中,他反復地籲請設議院、開國會,以行使立法權,使國民得與君主共議一國之政法。
他要求采萬國之良規以制定憲法,認為立憲法,確定君民權限,是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一個基本條件。為給立憲法找根據,他甚至牽強附會《春秋》的定“名分”,就是憲法的定權限。他還提出:中國歷來所無的民法、商法、訴訟法、軍律、國際法等等,西人皆極詳明,也宜采用。至於刑法,他也主張參酌羅馬法及英、美、德、法、日諸國法律,重訂施行。
康有為還以“公羊三世”說和天賦人權論為依據,闡述瞭法律的進化,指出法律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3個發展階段。在據亂世,國傢由一君獨治,人權沒有保障,律繁網密,違反人道,人們備受慘酷刑獄之苦。升平世的法律制度則優於前者,此時實行的是君主立憲或共和制,人權有保障,雖存在刑法但已去酷刑,廢死罪,人們已沒有據亂世刑獄的苦境瞭。但他認為最理想的乃是未來的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到那時,所有的人都享有充分的人權,沒有國傢,沒有帝王和行政長官,沒有傢庭,沒有私產,沒有犯罪,沒有刑法,刑措不用,囚獄不設,前二世存在的諸苦盡免。
在研究怎樣致刑措,免諸苦,達“大同”時,康有為還探討瞭犯罪的問題。他認為發生犯罪的原因,在於社會中存在著私產、貧困、君長等級與傢庭親屬關系等因素。因此,要消除犯罪,就必須去“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傢界”、“業界”等九界。要去九界,致刑措,又應從實現男女平等,“明男女人權始”。他設想,男女完全平等獨立,享有充分的“天予之人權”以後,便可從消除夫婦關系入手,進而消除傢庭、私產等,再進而消滅犯罪,去國界,而達到“大同”之世。
康有為在戊戌前後的數年間提出的這些法律思想,雖存在不少謬誤,但許多主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20世紀初,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高漲的新形勢下,康有為仍堅持保皇立憲,反對革命的立場,依然堅持社會改革隻能循序漸進,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隻能先行君主立憲,然後才可實行共和民主。“時有未可,治難躐級”,甚至認為在當時條件下,“行共和,言自由平等,則惟有破紀綱,壞倫紀,至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已”。與此相應,他的法律思想也從要求變革退而主張復古。他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的經義典章法度,是無數聖哲所創造,可行之久遠,不應完全廢除。他反對孫中山領導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甚至主張“舉辛亥以來之新法令盡火之而還其舊”。在這種保皇復古思想的支配下,他在1917年,與張勛合演瞭一出復辟醜劇。這個曾一度起過進步作用的人物,終於墮落瞭。
 康有為《大同書》手跡
康有為《大同書》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