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傢對食鹽徵稅和專賣榷禁的各種制度。中國鹽法,代有變遷,由簡而繁,由疏而密,日趨完備。唐玄宗開元以前為食鹽徵稅和專賣制度建立時期,開元以後為食鹽專賣制度日益完密的時期。
先秦 夏、商、周三代,鹽與其他土產一樣,大率是在產地徵稅,或作為土貢上繳國傢,聽民自由開採運銷販賣,實無專門鹽法可言。迄至春秋時期,管仲相齊桓公,興鹽鐵之利,國傢對食鹽的生產、銷售和買賣加以管理,開中國鹽法之始。。其法以官制食鹽為輔、民制食鹽為主,官收官運官銷,寓租稅於官府專賣鹽價之中,以增加國傢收入,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然春秋戰國時期,除齊國對食鹽實行專賣之外,其他諸侯國仍隻對食鹽征稅,唯稅率逐漸加重。史載秦自商鞅變法(見商鞅)後,賦鹽之利二十倍於古,鹽價昂貴,鹽商富累巨萬,人食貴鹽,小民貧困,至秦亡而未改。
漢 漢初開關梁山澤之禁,允許私人經營鹽業,國傢征稅,稅入歸主管皇室財產的少府,屬皇帝宮廷所有。諸侯王國亦得經營鹽業以自富,收入不歸中央。西漢中期,漢武帝劉徹內修法度,外開邊疆,頻年用兵,財用不足,於元狩年間(前122~前117)始將鹽業歸入中央的大司農,納入國傢財政,實行官營。在產區和主要中轉地設置隸屬大司農的鹽官,主管鹽的生產、分配及大規模的轉運。西漢末年,設置鹽官的郡國和縣共三十七處,分佈於二十七個郡國(見秦漢鹽官)。其官營辦法為募民制鹽、官收官運官銷。私自煮鹽受鈦(套在腳上的鐵器)左趾的刑罰,工具和產品沒官。鹽的銷售,或設肆售賣,或通過特許商人分銷。鹽的官營,增加瞭國傢財政收入,但鹽價逐漸昂貴,致有強迫抑配買鹽,私人鹽販乘機牟利,導致官鹽滯銷,鹽利所入不敷其費。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領大司農,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往各縣,平均調配,調節鹽價,濟以平準之法,弊始少革,國用乃贍(見兩漢平準)。漢宣帝時,賢良文學曾大力攻擊鹽鐵官營,致有鹽鐵之議。但事關財政收入,官營仍舊。東漢時,漢光武帝劉秀廢除食鹽專賣之法,罷私煮之禁,聽民制鹽,自由販運。於產鹽較多地區設置鹽官,征收鹽稅。其間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因財政困難,采納尚書張林建議,官自煮鹽,恢復漢武帝時期的官營辦法。漢和帝永和元年(公元88)即行廢止。此後,鹽官仍主稅課,鹽業民營,直至漢末。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時期,戰亂頻仍,官府對食鹽多行專賣,以敷軍國之用。魏有司鹽都尉、司鹽監丞,並遣使監督鹽官賣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還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資。蜀有鹽府校尉、司鹽校尉主管鹽政,鹽鐵之利,歲入甚多,有裨國用。吳設司鹽校尉、司鹽都尉管理鹽政,亦主專賣。
晉承魏制,仍實行食鹽專賣。鹽務隸於度支尚書,設司鹽都尉、司鹽監丞管理鹽政,規定不得私自煮鹽,犯者四歲刑。東晉遷居江左,軍國所需,隨其土地所出,以為征賦,對食鹽實行征稅制,歷南朝的宋、齊、梁、陳,沿而不改。北魏繼西晉對食鹽實行專賣,又仿南朝征稅制,屢興屢廢,乃無常制。534年,北魏分為東魏和西魏。西魏初行征稅制,後改為官營專賣,禁百姓煮鹽。北周繼西魏之後,繼續實行專賣。東魏和北齊則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對食鹽實行官營專賣。
隋唐 隋初鹽池鹽井皆禁百姓開采,由官府專賣食鹽。隋文帝開皇三年(583),開鹽池鹽井之禁,與百姓共之,廢除官賣,並免於征稅。至唐開元時期的一百三十年間,很少有征收鹽稅的記載,為中國食鹽無稅時期。
唐玄宗開元初年,始議榷鹽收稅。其後檢校海內鹽鐵之課,征收鹽稅。但各地鹽法並不統一。有設軍屯,由士兵生產軍用食鹽者;有官督私營,按等征課者;有按井納稅者;有免租納鹽者。法令疏闊,隻不過使鹽法從無稅轉向有稅而已。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財政陷入困境。天寶十五年(756),顏真卿於河北榷鹽以供軍需。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為鹽鐵使,總管全國鹽政,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並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盜煮私鹽罪有差”,創民制官收官運官賣的食鹽專賣制度。鹽利收入達四十萬緡。政府還在產鹽區設“監院”,管理鹽務,嚴禁鹽的私制私賣。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劉晏為鹽鐵使兼轉運使,再變鹽法,行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專賣制度:①在產區設置四個鹽場和十個鹽監,負責食鹽的生產和收購,切斷鹽商與鹽戶的關系,保證官府的專賣權。然後現場轉賣給鹽商,準其自由出售。商人如果以絹代鹽,每緡加錢二百。遂獲既推銷食鹽又收軍用絹帛之利。②在全國又設十三個巡院,負責推銷食鹽、緝查私鹽,兼管不設鹽監地區的產銷工作。③在重要地區設置鹽倉,常積鹽兩萬石,除賣給商人外,擔負平抑鹽價的作用,商人不至,則減價出賣。這些措施改善瞭民眾的食鹽供應,增加瞭國傢的財政收入。唐代宗大歷末年(779)鹽利收入達六百萬貫,“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唐德宗建中初年(780),劉晏去職,自此以後,鹽法混亂。官府不斷提高鹽價,至有以谷數鬥,易鹽一斤。官鹽既貴,私販公行。官府乃不斷整頓鹽政,鹽法日密。唐憲宗時開始劃定鹽商糶鹽區域,並嚴禁私鹽。其後犯私鹽均受嚴刑峻法懲處。然非但不能杜絕私鹽,反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唐末,王仙芝、黃巢均以販賣私鹽而積蓄力量,進而組織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使唐王朝走向崩潰。此外,唐後期因藩鎮割據,鹽利亦往往被地方勢力截留。
五代 五代鹽法逐年嚴密,成為人民一大禍害。後唐時全面榷鹽,劃區供應,對鹽的生產和經銷都作瞭嚴格的規定。凡官場賣鹽的地區,嚴禁私煎、私買、私賣,犯者處以嚴刑。又在鄉村創蠶鹽錢,於二月將鹽賒給鄉村人戶,五月絲蠶收獲時收回鹽錢,並嚴禁鄉村人戶將食鹽倒流城鎮。後晉初年,鹽禁較為松弛,取消官場賣鹽,允許商人貿易,由官府向民戶按戶等配征食鹽錢。其後取消商人賣鹽,重行榷禁專賣,而過去按戶等征收的食鹽錢仍然照征。後漢時更是全面禁止私產、私賣、私買,而由政府專賣,違者一斤一兩也要處死,成為中國歷史上鹽禁最嚴酷的時期。後周時雖逐步放寬鹽禁,但榷禁亦嚴,並一度在城鎮新增隨屋鹽錢。
宋 宋朝建立瞭更為完備的食鹽專賣制度。中央財政機構三司設鹽鐵使主管鹽政,直屬三司的京師榷貨務主辦鹽的專賣和鹽課收入。地方由朝廷委派高級官員或當地官員兼管鹽政。產鹽地設監置場,均派官管理鹽的生產。北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又在路一級設置提舉茶鹽司,主要鹽的生產和銷售。鹽的生產,一是官制,二是民制官收。官制食鹽皆召募農民,給口糧工錢,按年完成官定課額,全部食鹽歸官府。民制食鹽,專置戶籍,稱鹽戶,官給煮鹽工具和煎鹽本錢,免除科配徭役,隻以鹽貨折納二稅。鹽戶產量由官府定額,全部按官價收買。超產食鹽稱為浮鹽,略增價錢收買,任何人不得私賣。其食鹽銷售,宋初是“官鬻通商,隨州縣所宜”,沒有固定的制度。
官賣法就是官運官銷,鹽利收入主要由地方支配。宋初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食鹽都是實行官運官銷法。在東南漕運地區,利用運官糧的返程空船運輸官鹽,其他地區則派衙前、廂兵和征用民夫運鹽。鹽到州縣後由官府置場或設鋪出售。由於官鹽價貴質劣,民不肯買,往往強制抑配。售鹽辦法主要有令民繳納丁鹽錢的按丁配鹽法;二月育蠶時按戶配鹽,六月蠶事完畢隨夏稅用絲絹折納的蠶鹽法;按財產多少和戶等高下強迫購買一定數量食鹽的計產配鹽法;把一個地方的鹽利收入承包給商人,令其先納錢入官,準其領鹽販賣的買樸法。如此等等,弊病百出,殘害人民,引起反抗。加上朝廷擴大通商地區,增加中央鹽利收入,官賣法就逐漸被通商法代替。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官賣法隻在福建、兩廣一些地區繼續實行。
通商法是官府把官鹽賣給商人銷售,鹽利歸中央直接支配。它主要有交引法,鹽鈔法和鹽引法三種。交引法始行於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當時為解決沿邊軍需困難,令商人向邊郡輸納糧草,按地理遠近折價,發給交引作為憑券到解池和東南取鹽販賣。隨後又允許商人在京師榷貨務入納金銀錢帛和折中倉入納糧米,發給交引支鹽抵償。由於商人操縱物價,牟取暴利,虧損國傢鹽利收入,交引法逐漸被破壞,不能繼續執行。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乃行鹽鈔法。即按鹽場產量定其發鈔數量,統一斤重,書印鈔面。令商人在邊郡折博務繳納現錢買鹽鈔,到解池按鈔取鹽販賣。並在京師置都鹽院儲鹽,平準鹽價,鹽貴賣鹽,鹽賤買鹽,還允許商人憑鈔提取現金。這樣就保證瞭鈔值的穩定,保證瞭消費者和商人的正當利益。官鹽得以暢銷,鹽利得以增收。宋神宗時,東南地區也實行鹽鈔法,買解鹽發解鹽鈔,買東南鹽發末鹽鈔。末鹽鈔由京師榷貨務發行。崇寧以後,蔡京執政,鹽鈔法普遍推行於東南地區。隨著官府加緊聚斂,濫發鹽鈔,鈔與鹽失去均衡,商人持鈔往往不能領鹽。蔡京又印刷新鈔,令商人貼納一定數量的現錢,換領新鈔。此舉加重瞭商人負擔,並使鹽鈔失去信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蔡京乃創行鹽引法,用官袋裝鹽,限定斤重,封印為記,一袋為一引,編立引目號簿。商人繳納包括稅款在內的鹽價領引,憑引核對號簿支鹽運銷。引分長引短引。長引行銷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銷本路,限期一季。到期鹽未售完,即行毀引,鹽沒於官。故引仍是變相的新鈔,時鹽引又稱鈔引,隻不過在鹽鈔取鹽憑證的基礎上增加瞭官許賣鹽執照的性質,並在行銷制度方面更為嚴密而已。鹽引法在南宋一直繼續實行,唯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趙開在四川創行的鹽引法則略有不同。其做法是:井戶煮鹽不立課額,商人納錢請引,繳納引稅、過稅、住稅,向井戶直接買鹽出售。官置合同場負責驗視、秤量、發放,以防私售,並征收井戶的土產稅。廢除官買民鹽然後賣給商人的中介環節,直接征收井戶和鹽商的稅錢。
為瞭保證食鹽專賣制度的貫徹執行,官府還規定瞭各產地食鹽的販賣區域,越界、私賣、私制和偽造鹽引,超額夾帶食鹽者都予嚴懲。故宋朝鹽法較唐朝更為完備和嚴密,鹽利收入更成為國傢的一項重要財源。
遼金 遼朝對食鹽實行征稅制。在遼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使主管鹽政。會同初,後晉獻燕雲十六州,得河間煮鹽之利,又置榷鹽院於香河縣(今河北香河),但其制史無詳載。
金初循遼之舊,對食鹽實行征稅制。貞元二年(1154)始仿宋制行鈔引法,設官置庫,印造鈔引。在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七處設鹽鐵使司,負責批賣鈔引。各鹽場則設管勾等官負責監制和收納鹽斤。商人在京於榷貨務,在外於附近鹽司輸納現款,請買鹽鈔,即可赴鹽場支鹽,到劃定的行銷區域販賣,賣鹽後向地方州縣官繳引。鈔必須與鹽司的鈔引簿相符,引必須與州縣批繳之數相同。鹽載於引,引附於鈔。鈔以套論,引以斤論。如解鹽司以鹽一百五十斤為一席,五席為一套,一套為一鈔,一席為一引。凡商人買引者皆以引計。
元 元初政事簡易,未設鹽官,隻征收鹽稅。1230年始行榷法,沿金朝舊制設置鹽官制鹽,仿宋折中之法,募民入粟,或收現錢給鹽引支鹽。滅宋以後,復采宋制,專用引法。全國鹽務政令悉歸戶部。在主要產鹽區置都轉運鹽使司,非主要產鹽區置茶鹽轉運司或鹽課提舉司管理地方鹽務。並置批驗所批驗鹽引。鹽場則設官負責監制、收買鹽戶食鹽和支發鹽商食鹽。其賣引法為戶部主印引,鹽司主賣引。鹽司按銷鹽狀況確定引額,由戶部按額印造,頒發各區鹽司收管。賣引用鹽司鈐印,據行鹽區域和規定的引價,隨時填寫發賣。每引一號,書前後兩券,用印鈐蓋其中,折一為二,以後券給商人,謂之引紙,以前券作底簿,謂之引根。商人持引紙到鹽場,鹽官檢驗相符,於引背批寫某商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場支鹽出場,即可將鹽運到行鹽地區售賣。鹽場鹽袋由官監制,按每引額重四百斤裝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過。並在鹽袋上書名編號以防偽冒。凡商人運鹽至賣鹽地區,必須先行呈報,由運司發給運單,蓋印後寫明字號、引數、商號和指定銷鹽縣份。沿途關津,依例查驗,驗引截角。每引一張,運鹽一次,鹽已賣盡,限五日內赴所在地方官繳引,違限不繳,同私鹽罪。其立法比宋更為嚴密,故引法起源於宋,完畢於元。鹽法既密,導致引價日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鹽一引,值中統鈔九貫,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每引增至一百五十貫,造成官鹽既貴,私鹽愈多。加之軍人違禁販運,權貴托名買引,加價轉售,而使官鹽積滯不銷。於是官府又擴大官賣食鹽區域,強配民食,不分貧富,一律散引收課,農民賣終歲之糧,不足償一引之值。元惠宗至正年間(1341~1368)雖罷食鹽抑配,然民困已深,禍機已伏,鹽販張士誠、方國珍與其他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元朝遂亡。故史傢謂元朝亡於鹽政之亂。
明 明朝鹽法,初承元制,其後略有變動。中央戶部隻頒給鹽引,審核解部課銀,稽核奏銷,辦理考績。鹽務行政分於地方。另設巡鹽禦史,或由巡河禦史、按察史兼中央特派員監督地方鹽務。產鹽地區設都轉運鹽使司或鹽課提舉司,並下設分司,主管鹽務。鹽場則設鹽課司主食鹽的監制收買支賣事宜。其鹽法除在某些地方按戶收取糧、鈔的戶口配鹽法及官吏以鹽折俸法外,主要行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開中法”和民制商收商賣的“綱法”。
開中法,又稱開中,即召商納糧、納馬、納鐵、納帛、納銀等官需之物,而以納糧為主,易之與鹽。凡邊地缺糧,由戶部出榜召商,赴邊納糧。仍先編制二底簿,分立字號,一發各佈政司及都司衛所等收糧機構,一發各鹽運司及提舉司等鹽務機關。俟商人納糧,即由收糧機關填寫納糧數、應給引數、鹽數,並填給倉鈔,由商人持其至鹽務機關經檢驗相符,則按數給引,派場依次支鹽,按區行銷售賣。其檢放、截角、繳引及途程等手續均與元朝相同。開中法實行初期,商人並就邊地召民墾種,謂之商屯。寓屯於鹽,收轉運省、邊儲充和殖邊開邊之效。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但永樂以後專於北京等少數地區開中,其餘各處相繼停止,已失開中實邊初旨。明中葉以後,權勢豪要紛紛以納糧、納銀占中鹽引,然後賤買貴賣,遂使商人失利又難以按時支鹽,從而影響商人納糧報中,致邊地商屯盡廢。明英宗正統初,因商人赴各場支鹽,多寡懸殊,乃創“兌支”之例,如淮浙鹽不敷分配,則準持引赴河東、閩廣諸場支取;不願兌支者聽其守支。這種辦法仍無法解決商人支鹽的矛盾,正統五年(1446)乃將食鹽分為“存積”和“常股”兩部分。常股價賤,由守支商人依次支鹽;存積價貴,邊事有急,召商人入中,引到即支。存積與常股鹽一般維持三七或二八的比例,後來存積鹽的比例稍有上升。存積鹽的設置並沒有緩解開中法的危機,反而使常股鹽壅滯、兌支制度加強,破壞瞭原定支鹽地域界限,並產生出“代支”制度。代支即鹽商幾年幾十年支不到鹽,年久物故,允許親屬繼承支鹽權。於是又產生瞭有的商人把引目與人的“夥支”,把引目典當與人的“賣支”,委托別人販賣,坐收鹽利。這樣,代支的出現就使單一的開中商人分化為專以報中售引為業的邊商和以守支販鹽為業的內商。邊商成為糧商和引商,內商才是經營鹽業的鹽商。由於內商之鹽不能速得,邊商之引不願賤售,報中無人,存積鹽滯銷,致邊儲無著。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式實行開中折色,召商納銀,匯解國庫,分給各邊以濟軍餉。加上弘治二年(1489)因無鹽支給鹽商,實行餘鹽開禁,允許鹽商購買灶戶正課之外的餘鹽以補正鹽之缺,令灶戶每引交銀後直接賣鹽與商人,更加引起私鹽泛濫。而官府對灶戶的剝削,造成灶戶破產,官課正鹽逐年減少,更完全動搖瞭開中法的基礎。
綱法行於明神宗萬歷四十五年(1617),即為銷積引,將商人所領鹽引編成綱冊,分為十綱,每年一綱行稅引,九綱行現引。冊上有名者具有世襲包銷權利。其後,官不收鹽,令鹽戶將應納課額,按引繳銀,謂之“倉鹽折價”。官府賣引,由商人自行赴場收運,政府將食鹽收買運銷之權悉歸商人。從此開中法廢綱法興,確定瞭鹽法中的商買商賣的包銷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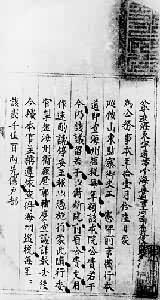 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海蓋兵備道呈海州鹽稅書冊
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海蓋兵備道呈海州鹽稅書冊
清 清朝中央戶部管理全國鹽務,鹽政之權分於各省。初差禦史巡視,後改歸總督、巡撫兼管,終則設置鹽院。產鹽地區設都轉運使司,或以鹽法道、鹽糧道、驛鹽道、茶鹽道兼理鹽務。鹽運使以下分別置官設署掌政令、征課、批引、掣放等鹽務。其鹽法以繼承明末官督商銷的綱法行之最久。
官督商銷,即召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見鹽商)。商人向政府繳納引稅後領取鹽引,買鹽及銷售均有地點限制。鹽商中收鹽者為場商,行鹽者為運商。運商中又分引商、運商。引商均子孫世襲,稱為“引窩”,壟斷鹽引購買權,大都脫離流通過程,靠出賣鹽引,坐收“窩價”為生。運商活躍於流通領域,壟斷鹽的運輸和銷鹽地區的引岸權。運商中又有總商和散商之別。散商即個別的鹽商,總商即散商的首領。官府把散商隸總商名下,總商負督征鹽課和查禁私鹽之責,並將散商花名引數送鹽政衙門備案,然後按所領引數行鹽納課。官督商銷使專業鹽商壟斷瞭鹽的收買、運輸和銷售,得以任意剝削食鹽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隨著官府財政的需要,不斷增引加課,雍正時又開“報效”之例,每遇軍興、慶典、營建,皆令鹽商捐資。國傢為獎勵鹽商,初則準其加價,繼則準其加耗。加之官吏勒索成風,私鹽盛行,鹽法紊亂,商民皆受其害。於是從雍正時起,在一些地區陸續對鹽法進行改革。或廢引截商,官運官銷,或將鹽課攤入地丁,就場征稅,聽民運銷。道光十一年(1831),遂在主要產鹽區行票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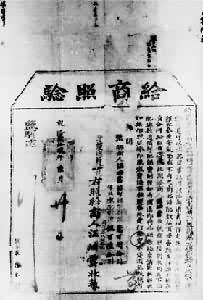 清兩浙鹽運道發給鹽商江岫雲的執照
清兩浙鹽運道發給鹽商江岫雲的執照
票鹽法,即取消鹽引私引商,設督銷局,招販行票,在局納課,領票買鹽,直赴運岸行銷。票鹽法廢除瞭引商、運商對食鹽的壟斷,具有降低鹽價、打開銷路及增加鹽稅等作用。咸豐以後,百貨抽厘亦及鹽務,謂之“鹽厘”,鹽課收入,恃鹽厘為大宗。厘金征收方法有包辦和散收。包辦即由會館或同業公所向厘金局承納包額,商民可免厘金局留難殊求;散收即各厘金局直接向貨主個別征收。同治三年(1864)整頓兩淮票法,聚多數散商為少數整商。五年,李鴻章在淮南行循環票法,鹽商隻要能照章完納鹽厘,即可享受循環運鹽之權,不準新商加入。從此,票商專利同於引商。光緒年間,因賠款、練兵、要政、海防、興辦鐵路等名目而增收鹽厘,數逾正課。自此鹽價日貴,私鹽日甚,引岸多廢。省亦各自為政,或官運,或民運民銷,或官運商銷,制度不一,但仍以官督商銷為主。鹽商專利之弊,與清朝相始終。
民國 1913年,在中央的財政部設鹽務署和稽核總所分管鹽政和稅收。鹽務署的下屬機構有產鹽地區的鹽運使司,並在鹽場設場知事,掌鹽務行政、產制貯藏、倉坨鹽警、鹽督捆運、征收場課;銷鹽地區的榷運局主管收鹽發鹽。稽核總所的下屬機構有產鹽地區的稽核分所,銷鹽地區的稽征處、收稅總局,主管收稅放鹽。時值袁世凱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瞭善後借款合同,以鹽稅為擔保。按照合同規定,鹽務稽征總所及其所屬機構必須聘請外籍人員分掌鹽務;征收的鹽款不得存入銀行團之外的銀行,非經外籍任職人員簽字不能提取,致使中國的鹽政主權落入外人手中。1917年以後,善後借款本息改由關稅支付,1928年國民政府始將鹽稅存款改存中國銀行,收回鹽政主權。1932年和1935年政府曾對鹽務機關進行改組,擴大鹽務稽核總所職權。1937年再次改組鹽務機關,鹽務稽核總所改為鹽務總局,直隸財政部,綜理全國鹽務,於產鹽地區設鹽務局、銷鹽地區設鹽務辦事處。撤銷原鹽務署,財政部設鹽政司,專司指導與審核事宜。
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省自為政,鹽法紊亂較晚清為甚。其後逐漸建立鹽法制度,規定非政府許可不得開采。政府於鹽場適宜地點建立倉坨儲鹽,鹽場所制之鹽必須全部存於指定的倉坨,由政府檢查質量,秤發出納,就場以百擔為單位征稅。商人買鹽須先向代理國庫銀行納稅,領取完稅憑證後再至倉坨買鹽。倉坨出售之鹽,由場長召集全體制鹽人代表,按等議價公佈。鹽商在產區繳納之場稅及中央附加稅稱正稅,銷區繳納之岸稅及中央附加稅稱銷稅。政府還建立鹽警緝查私鹽。其運銷制度,在稽核總所成立初期,雖曾在一些地區取消票權,開放自由貿易,但難於在全國推行,不少地區仍然實行專商包運包銷的引岸制。鹽稅稅率,據30年代統計,約占鹽價的四分之三。抗日戰爭爆發後,政府加強瞭對食鹽的官運官收,以增加收入。內戰爆發後,民國政府更是不斷增加鹽稅,以挽救其財政崩潰。
參考書目
曾仰豐:《中國鹽政史》,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
陳詩啟:《明代的灶戶和鹽的生產》,《廈門大學學報》第1期,1957。
楊德泉:《清代前期兩淮鹽商資料初輯》,《江海學刊》第11期,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