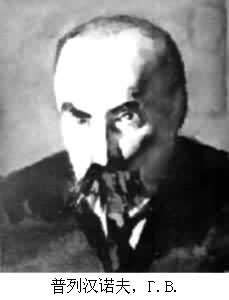 Г.В.普列漢諾夫
Г.В.普列漢諾夫
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傢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傢。1856年12月11日生於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父親是貴族地主,母親是俄國民主主義思想傢В.Г.別林斯基的後裔。普列漢諾夫大學學時代曾參加民粹主義小組,1880年亡命西歐,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883年組織“勞動解放社”。1900~1903年和列寧合作編輯出版《火星報》,積極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建工作。1903年11月轉向孟什維克,從此政治上走上瞭機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在1905~1907年革命中,作為孟什維克的思想領袖,在一系列策略問題上采取瞭右的立場。斯托雷平反動年代(1907~1911),為瞭保衛黨,保衛地下活動,他同佈爾什維克結成瞭反對取消派的戰鬥聯盟。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又變成瞭一個為帝國主義戰爭辯護的狂熱的社會沙文主義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的勝利,結束瞭他37年的流亡生活。回國以後他的政治立場並無變化,始終不理解,也不贊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918年5月30日在孤獨中病逝。遺體遵照本人願望安葬在列寧格勒沃爾柯夫墓地別林斯基墓旁。
與復雜多變的政治生涯不同,普列漢諾夫的哲學道路自從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是始終如一的。他一貫忠誠地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對唯物史觀的發展作出瞭貢獻,他的許多著作精彩地極有說服力地宣傳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890年他發表瞭第一篇哲學專論──《評梅奇尼柯夫的書》。19世紀90年代是他最富於創造性成果的多產歲月。1895年問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標志著他一生理論思維的最高峰。此後又繼續發表瞭大量的哲學論著。他的主要哲學著作還有:《黑格爾逝世六十周年》(1891)、《唯物主義史論叢》(1896)、《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1898)、《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1899~1900)、《反對哲學的修正主義》(論文集,1898~1910)、《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車爾尼雪夫斯基》(1890~1892、1894、1909)。
哲學思想
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貢獻 普列漢諾夫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即辯證唯物主義,並對它的基本特征、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內容和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作瞭全面、詳細的論述。
普列漢諾夫認為,哲學的任務是“研究認識和存在的根本原理並根據這些原理來瞭解一切實在的東西”。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的研究對象始終在不斷地變化著。古代的哲學是無所不包的,文明的進步使得各門具體科學相繼脫離哲學而獨立。然而從哲學母體中孕育出這些獨立科學隻是哲學的天職之一。它還有一項同樣重要,也許越來越重要的任務,就是從根本上總結和概括各門具體科學的成果。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迅猛發展,可供哲學進行理論概括的材料與日俱增。研究對象的不斷縮小和急劇擴大,是哲學發展過程中並存的、不可分割的,而且至今沒有結束的兩個方面。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唯物主義傳統的卓越代表,他非常重視辯證法,通俗地解釋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批判唯心主義、二元論和形而上學思想時提出瞭許多富有獨創性的新論據;詳細考察瞭馬克思辯證法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批判繼承關系,駁斥瞭把兩者混為一談的錯誤;充分揭示瞭辯證唯物主義作為“革命代數學”和“行動哲學”的認識意義和實踐意義,根據它的基本原理正確分析瞭19世紀末俄國社會經濟問題,給俄國革命者指明瞭道路;創造性地研究瞭多種思想體系,包括歷史觀和哲學史本身,以及俄國社會思想、美學、無神論、倫理學和它們的歷史。
普列漢諾夫把認識論看作“完全次要的問題”,因而妨礙他用更多的精力去深入探討認識論問題。但是在物質和世界可知性、感覺與經驗、空間與時間、原因與結果、必然與自由、真理與實踐等一系列問題上,他熱情地捍衛和廣泛地解釋瞭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瞭當時各種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理論,提出瞭不少令人信服的新論據和獨到的見解,並且對17、18世紀以來西歐主要哲學傢們的認識論學說進行瞭認真分析,得出瞭一些新結論。他明確提出和論證瞭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史觀二者一致的思想。這些論據、見解和結論,大部分經過加工後為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所吸收。他用“象形文字”比喻感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認為二者不是絕對一致的,是一種用語上的混亂。這種說法同符號論不易劃清界限,因而受到瞭列寧的批評。
普列漢諾夫十分重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指出這是由它的階級性和實踐性決定的。他還考察瞭如何正確運用它的一般方法論原則,比如整體性原則、發展原則、歷史主義原則和黨性原則,以及方法的適應性從屬於主觀目的和客觀條件的原則等。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又一貢獻。
在歷史觀上的貢獻 歷史觀是普列漢諾夫一生哲學研究成果最豐碩的領域。他把辯證唯物主義運用於認識社會生活,得出社會革命合乎規律和必不可免的結論。他在歷史觀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具體化和發展瞭馬克思的學說,提出許多新原理和新思想。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一般社會學理論,是在統一中研究社會的結構、社會及其諸要素的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特別是研究社會發展動力的科學。他提出著名的“五項”論,認為社會結構中存在著生產力、經濟關系、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心理”和思想體系等五項主要因素。它們之間有一種起源關系,即前面一項決定著後面一項,而後一項對前一項又有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生產力或經濟因素歸根結柢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它對其他因素有直接影響,隨著文明的進步,影響將越來越由直接變為間接,即要通過越來越多的中介環節。這些中介環節構成極其復雜的力量體系。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有多少,中介環節就有多少。社會越發展,中介環節就越多,經濟的決定作用就越間接。在不同歷史條件下,這些環節的相對重要性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普列漢諾夫在反對各種唯心史觀和因素論等思想的同時,特別強調批判社會學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但他充分論述瞭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明確表述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以生產力為中介,並隨生產力的性質、規模、水平的不同而變化。他把生產關系區分為“技術關系”和“財產關系”兩類。前者指人們在同自然作鬥爭過程中所結成的關系,它基本上“與生產力的發展相平行地改變”;後者則不同,它往往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隻有當這種落後達到一定程度時,它同生產力以及上述“技術關系”的矛盾才是引起社會革命的根源。普列漢諾夫多次指出,在不同條件下社會存在的不同因素,如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鬥爭等對特定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並不都是同一的,有時一種因素的影響最突出,有時另一種因素的作用更明顯。但這種情況絲毫沒有推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恰恰相反,而是更充分地證實瞭唯物史觀的一元論性質。在馬克思主義文獻史上,他第一次明確提出瞭社會意識兩種基本形態的學說。他稱低級形態的社會意識為“社會心理”,高級形態的社會意識為“思想體系”(包括自然科學)。任何形式的思想體系反映社會存在,都要依據心理和概括心理。他強調:如果不精細地研究和瞭解“社會心理”,對社會生活和歷史事件、對思想體系的歷史的唯物主義解釋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還創造性地發展瞭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學說,認為偉大人物的歷史作用不能決定歷史事變的一般方向,隻能影響事變的個別外貌和某些局部後果;這種影響的可能性和范圍還要依當時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對比關系來決定;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主要不在於他能決定事變的個別外貌,而在於他最能致力於為當時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響下所產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這些思想比P.拉法格、F.梅林、A.拉佈裡奧拉等第二國際理論傢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更準確,同時大大地擴展瞭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范圍。
在哲學史研究上的貢獻 普列漢諾夫對哲學史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他一生研究得最精深、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主要是18世紀法國哲學、德國古典哲學、19世紀西歐空想社會主義以及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他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是“人類思想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偉大的革命”,這個革命是在批判地接受、改造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實現的。他特別論證瞭唯物史觀的發現是歷史觀發展中繼承性和變革性的統一。他指出,素樸形態的唯物史觀,或者說科學的唯物史觀的因素,是和唯心史觀一樣的古老,它源遠流長,支派繁衍,內容極為豐富,科學的唯物史觀隻是迄今為止唯物史觀的最高發展。如果弄不清馬克思以前至少100年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不明白歷史觀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變革,就不可能真正科學地論證唯物史觀的產生是一場偉大革命。
倫理思想 普列漢諾夫在捍衛和論證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理論的鬥爭中,闡發瞭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基本觀點,為鞏固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促進真正科學的道德學說的建設,起瞭重要的作用。普列漢諾夫的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唯物主義史論叢》、《論所謂俄國的宗教探索》等著作中。
普列漢諾夫強調運用唯物辯證法考察社會的道德現象,認為在道德領域,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方法最清楚地表現出它的優越性。他運用這一方法,分析瞭社會結構諸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具體闡發瞭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的基本觀點。他指出,一定發展程度的生產力決定一定的生產關系,社會的道德狀況乃至整個精神狀況,是同表現這種關系的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並同其他社會意識形式相一致。就一個民族的國傢制度和這個民族的道德風尚、習俗來說,他認為兩者是彼此影響、互相作用的,同時又強調它們歸根結柢都要由社會的經濟結構來說明。普列漢諾夫還深入闡述瞭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的基礎或道德與利益關系的觀點。他批判倫理思想史上把不變的人性看作道德基礎的錯誤觀點,指出人類道德的發展,每一步都伴隨著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的實際需要。他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也應當說,利益是道德的基礎。他基於對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科學理解,進一步強調指出,道德的真正基礎在於追求整體的幸福,即追求部落的、民族的、階級的、人類的幸福。他既反對那種否定道德與人們實際利益有聯系的觀點,也反對那種認為道德受利已主義的考慮所制約的觀點。
普列漢諾夫聯系階級鬥爭考察道德的發展,認為道德的發展是不以個人的意志和理性為轉移的,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始終在道德發展中起著主要作用。他揭露瞭資產階級道德狹隘的階級性及其在實踐中的虛偽性,闡述瞭無產階級道德產生的必然性,認為無產階級道德理想的形成,是同這個階級的社會地位緊密相聯系的,是與社會的經濟現實相符合的,是以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為基礎的。道德的自由活動,就是人們在實現這種具有必然性的理想時的自覺活動的表現。他還指出,道德按其本性來說,與對超自然物的信仰並無聯系,把道德與宗教扯在一起的唯心主義觀點,實質是通過宗教把統治階級的道德神聖化。此外,他還批評19世紀俄國著名文學傢Л.Н.托爾斯泰關於寬怒一切的愛和不用暴力抗惡的學說,揭露瞭修正主義者和新康德主義者用唯心主義倫理理論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企圖,表現瞭他反對倫理社會主義的立場。
普列漢諾夫在其活動的後期,試圖通過引證簡單的道德準則,為他的護國主義立場及其對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辯護。
美學思想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第一個將馬克思主義觀點用於美學和藝術理論的人。從19世紀80年代起,普列漢諾夫批判地繼承瞭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美學、文藝理論的傳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人類的審美活動和藝術現象,在和唯心主義思想的鬥爭中,堅持和發展瞭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本原理。
審美觀念、藝術活動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及社會心 理的關系 普列漢諾夫依據大量的事實材料,證明審美觀念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種決定作用往往通過社會心理來實現。
普列漢諾夫認為,要說明人類的美感的起源,必須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進行研究。美感,不隻在文明人那裡,就是在野蠻人那裡也是和復雜的觀念聯系在一起的。野蠻人用來裝飾自己的那些東西是和富有的觀念或迷信的觀念相聯系的。裝飾物往往由於和復雜觀念的聯想才顯得美。當裝飾品開始以它的樣子引起人們愉快的感覺,而不是想到它的實用價值的時候,它就成為審美快感的對象,它的顏色和形式就具有巨大而獨立的意義。當某種東西在原始人的眼中獲得某種審美價值以後,人們僅僅為瞭這一價值去獲得它,而忘掉瞭它的價值來源。
普列漢諾夫認為,即使在原始狩獵社會裡,技術和經濟也不總是直接決定審美趣味的。在文明民族那裡,藝術對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的直接依賴性消失瞭,藝術和社會經濟的因果關系變得更復雜、更曲折、更模糊,社會經濟常常通過政治、心理、道德、哲學等因素來影響藝術。他強調心理的因素,認為藝術同社會心理有著廣泛密切的聯系,研究藝術必須研究社會心理。我們的祖先在還隻是“類似”人的時候,就已經是社會的動物瞭,人的心理的生理的本性,使人能夠有審美的趣味和概念。人的本性、習慣和意向、觀點和理想、同情和反感都是隨著歷史發展的進程而改變的。它的變化顯然有著某種外在的原因,歷史學傢和社會學傢應當找出引起它發生變化的那些原因,人的心理本性的活動在任何時代都不會停止。但在不同時代,由於社會關系不同,進入人的頭腦裡的材料不同,加工的結果也就完全不同。心理現象的這整個復雜的辯證法的基礎就是社會方面的各種事實。社會關系決定著社會心理,而社會關系是在經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
藝術和審美趣味的社會制約性 普列漢諾夫認為藝術主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是生活機構中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唯有考察瞭這個原動力,並研究瞭階級鬥爭的種種不同變化,才能夠弄清楚階級社會的藝術發展的歷史。藝術史是通過階級鬥爭這個中間環節與經濟史相聯系的。
普列漢諾夫以法國藝術史為例,說明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審美趣味的更替受階級鬥爭的制約影響。在繪畫領域,當法國第三等級要求革命的時候,他們仇恨表現貴族情調的佈賽派,強調對古代英雄的崇拜,於是就產生瞭大衛派。革命之後,第三等級的經濟要求得到瞭滿足,便開始懼怕變革,大衛派的畫法也趨於墨守成規,從革新派變為保守派,很快沒落下去。在戲劇領域,起初在舞臺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古典主義悲劇,它迎合當時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禮儀制度和宮廷生活風尚,表現貴族階級的觀點、趣味和願望。隨著封建君主制度的削弱和貴族階級的衰微,古典主義悲劇開始讓位給流淚喜劇。“流淚喜劇”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肖像,它的興起乃是法國資產階級成長的結果。隨著法國資產階級的壯大,流淚喜劇重新讓位給古典主義悲劇。雖然還是悲劇的形式,內容卻不再表現貴族趣味,而是借助古代英雄人物來體現資產階級的共和理想,成為鼓吹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口號的工具。在文學的舊瓶裡裝進瞭全新的革命的內容。審美趣味的更替取決於階級鬥爭的進程。
普列漢諾夫認為任何文藝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它的內容和形式都反映出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和幢憬。愈是大作傢,他的作品受時代的影響也就愈明顯。藝術傢的獨創性正表現在他比別人更早、更好、更充分地表現出他那個時代、社會的需要和憧憬。
普列漢諾夫認為,藝術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手段之一。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和思想賦予一定的形象表現出來,就開始誕生藝術。在大多數場合下,人們的藝術活動,目的在於把自己反復感到和反復想起的東西傳達給別人。在階級社會裡,這種交往的可能性,受到階級關系以及各個階級所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當資產階級處於上升的時期,他們的先進思想傢,同時也是除瞭特權階級以外的整個民族的思想傢。那時候以具有資產階級觀點的藝術作品為手段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范圍,比較起來是很寬廣的。但是,當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全體群眾的利益相不一致的時候,特別是當資產階級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發生瞭不可調和的沖突的時候,這種交往范圍就顯著地縮小瞭。藝術作品的價值歸根結柢取決於它的內容。資產階級的藝術隨著這一階級的日益接近滅亡而逐漸失去它的內在價值。滿足於從神秘主義、象征主義以及其他類似的“主義”中借取代用品,使得現代資產階級藝術進入衰落的過程。
普列漢諾夫指出,任何一個多少有點藝術才能的人,隻要具有時代的偉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會大大地增強。隻是必須使這些思想成為他的血肉,使得他象一個真正的藝術傢那樣把這些思想表達出來。
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批判 普列漢諾夫認為,藝術是一種社會現象,藝術傢是為社會而存在的。藝術隻有在描述、喚起或表達那些對於社會有重大意義的動作、感情和事件的時候,才獲得社會的意義。
藝術不僅是生活的簡單反映、再現,也不隻是判斷生活,認識現實,在藝術中往往融合著理想。藝術不應滿足於檢驗現在存在的東西,藝術應當促進人的意識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改善,應當具有改造現實的積極作用。
為藝術而藝術論者認為:藝術本身就是目的,把藝術變為手段以求達到某種不相幹的、即使是最崇高的目的,那就等於降低藝術作品的價值。普列漢諾夫通過對藝術史的分析,指出這種理論是在藝術傢和他們周圍的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不協調的地方產生的。在亞歷山大一世的時代,普希金並不擁護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但當尼古拉一世想把普希金變成現存社會的歌頌者的時候,他和宮廷貴族和政界人物產生瞭不協調,他寧願逃遁到藝術中去,變成瞭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的擁護者。在這種情況下,與環境的不協調,就會對藝術產生有利的影響。普希金這種超脫,意味著他對反動統治者的消極反抗。但在一般情況下,鼓吹為藝術而藝術是對社會利益的漠不關心。這種理論容易使藝術傢看不見社會生活,而無謂地糾纏在毫無內容的個人體驗和病態的空幻臆造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真正的為藝術而藝術,實際上不可能實現。帕拿斯派詩人和早期法國現實主義者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熱烈擁護者。他們雖然反對當時社會環境的庸俗習氣,卻一點也不反對作為這種庸俗習氣基礎的社會關系。他們一面詛咒“資產者”,一面卻尊重資產階級的制度。而且隨著歐洲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解放運動的加強,他們對這種制度的依戀變得越來越有意識,就越難於堅持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反而變成資產階級制度的有意識的保衛者。現代資產階級唯美主義者雖然口頭上反對小市民習氣,但他們對金錢的崇拜並不亞於最平庸的市民。把“自我”作為“唯一的現實”的藝術傢,為瞭愛自己而把金錢和藝術交織在一起,為藝術而藝術變成瞭為金錢而藝術。
功利主義藝術觀與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相對立。普列漢諾夫認為,對功利主義藝術觀也要作具體分析。任何一個政權為瞭本身的利益,都對藝術采取功利主義的態度。由於過去的政權隻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保守甚至是反動的,因此功利主義的藝術觀並不是革命者和一般具有先進思想的人們所特有的。在第二帝國的法國作傢當中,有一些人,如亞歷山大、小仲馬、拉馬丁等,他們之所以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並不是想用什麼新的社會制度來代替資產階級制度,而是想鞏固被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大大動搖瞭的資產階級制度。可見,功利主義的藝術觀不論與保守的情緒或革命的情緒都能很好地適應。
普列漢諾夫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藝術和審美現象所作的分析,取得瞭可貴的成果。他的藝術理論及文學批評的著作包含著非常寶貴的有些簡直是出色的見解。他對馬克思主義美學、藝術理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論述,在他的全部理論遺產中占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地位,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歷史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在俄國影響深遠,“培養瞭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曾受到早年普列漢諾夫哲學上多方面成就的影響。列寧再三強調必須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主張把他的全集中的所有哲學文章匯編成冊,列為“必讀的共產主義教科書”,並多次高度贊揚他在1883~1903年間的哲學功勛,還把他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俄國先進階級的哲學“整頓”中所起的偉大作用,比之為18世紀百科全書派在法國,或者象從I.康德到G.W.F.黑格爾、L.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在德國所起的那種作用。同時,列寧也尖銳地批評普列漢諾夫的種種失誤,認為他的根本的哲學錯誤在於沒有把辯證法看成是一門系統的哲學科學,沒有把作為邏輯的辯證法理論當作專門研究的對象,沒有真正深入到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寶庫中去作一番切實的探討。他沒有足夠地註意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對這個論斷的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也沒有註意。他在後期的政論中甚至把這一辯證規律當成瞭實例的總和。同時他也沒有註意到在黑格爾哲學中有一個和辯證法融為一體的認識論系統,特別沒有註意到黑格爾關於邏輯和歷史、抽象和具體、一般和個別、絕對和相對之間辯證關系的理論。因此,他在批判新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時過多地把註意力放在一般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上,不善於根據人類認識的最新成果來豐富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容,改變它的某些形式,把辯證法進一步貫徹於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各個方面,特別是不善於把馬赫主義、新康德主義及其他唯心主義思潮同當代物理學危機聯系起來考察。
普列漢諾夫逝世後,根據列寧的倡議,蘇聯學者在保護、收藏、整理、利用他的著作、手稿、筆記、批註、來往書信等方面做瞭大量的工作,先後出版瞭全集24卷,其中有:勞動解放社文集6卷、與Л.В.阿克雪裡羅得通訊集2卷、遺著8卷、哲學選集5卷、哲學遺著3卷。
20世紀20年代普列漢諾夫的著作開始在中國翻譯出版。最早的中譯文是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2月27日在北京《晨報》斷續連載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1929~1930年,幾乎他的全部最重要的哲學著作都有一種或多種中譯本。魯迅、瞿秋白、博古等在翻譯介紹他的美學和哲學思想著作方面作出瞭重大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普列漢諾夫著作得到大量翻譯出版,其中包括他的5卷哲學選集。這些著作的譯文共約580餘萬字。其字數在所有中譯的外國哲學傢著作中,僅次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
參考書目
Μ.約夫楚克、И.庫爾巴托娃著,宋洪川等譯:《普列漢諾夫傳》,三聯書店,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