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府設置的一種供使臣出巡、官吏往來和傳遞詔令、文書等用的交通組織。始於春秋戰國,稱遽、馹(古代驛站專用的車)、郵、傳等。《左傳》中有關記載不少,《孟子·公孫醜》也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可見當時郵驛制度相當發達。
秦漢 秦平定六國前後,由於統一和中央集權的需要,驛傳制度已很完備。據《晉書·刑法志》所載《魏律序》雲,秦代有廄置、承傳、副車、食廚等有關驛傳的法律。睡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許多部分都有驛傳及其制度的記載。
漢承秦制,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當時,用車傳送稱“傳”,用馬傳送稱“驛”,步遞稱“郵”,三種稱呼常通用,也稱為“置”。
漢代驛傳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幾十裡置一驛(一般為三十裡左右),即供應人夫車馬和食宿的交通站。驛有傳舍,可供歇宿。各級來往人員及其從者的膳食和驛馬的飼料,都有一定的標準。持有官府頒發的符、傳,過所的旅客都可在傳舍止息。驛與驛之間或不設驛的一般道路上,則由主察奸盜的亭兼管文書傳遞。十裡一亭,五裡一郵。亭也可止宿。文書由驛及亭、郵傳送,有很具體的規定。例如文書的傳遞,舉凡傳遞的方向,文書的性質(書檄、詔書等),封數及其裝束,發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單位或人員,傳受的郵站及其吏卒姓名,郵站收發時刻,規定的裡程和時程,傳送的方法(如郵行、亭行、次行、吏馬行)等,都要做詳細記錄,即“郵書課”。不按規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罰。緊急文書則由驛騎持赤白囊遞送,稱“奔命書”。除文書傳遞、官吏往來外,方士、賢者有詔命征召的,也得乘傳;吏民告急上變的,亦可要求借用軺傳至京師言事。
 漢“傳舍”印章封泥
漢“傳舍”印章封泥
 漢“傳亭”印章封泥
漢“傳亭”印章封泥
中央政府中管理驛傳的部門,西漢不詳,東漢時為太尉屬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屬下亦有法曹,但從漢簡的記載看,郵驛事務至少在邊郡系屬都尉管理。驛的主管官員為置尉、置佐、驛候、置候、驛丞,下屬有驛小史、傳舍鬥食嗇夫等。驛傳所需人夫車馬由官府置備,但也有征發民夫和民間車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傳車和驛馬。使用時按官職高低、任務輕重和時間緩迫分為不同的等級。四馬高足(好馬)稱“置傳”,四馬中足稱“馳傳”,四馬下足稱“乘傳”,一馬二馬的為“軺傳”,急事騎一馬稱“乘”。在個別情況下,傳車馬匹可超過規定,最多的達七乘傳。使用驛傳需持政府頒發的一尺五寸長的木傳信,封以禦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車馬的等級,從一馬一封到置、馳傳的五封不等。東漢時為節省費用,則往往但設騎置而無車,由於法律規定驛傳隻能用於公事,西漢大貴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驛傳的。
驛傳效率很高,西漢時,從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到長安,公文往返隻需七天。東漢時,奉天子璽書使者三騎行,一晝夜可達千裡。這就大大便利瞭政令的傳達和各地的聯系,起瞭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傢的效能。驛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於人民的往來和各地經濟的交流。隨著漢朝勢力的向外發展,漢政府把國防設施和交通郵遞結合起來,加強瞭邊疆地區驛傳的建設。漢武帝通南夷,從元光六年(前129)起沿途置郵亭。張騫通西域後,酒泉亭障展築到玉門,後又延伸到鹽澤(今新疆羅佈泊),以後直到東漢,這帶地區仍是“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驛傳制度不僅加強瞭內地與邊疆的聯系,有利於國防,也對漢族與邊疆各族以及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瞭積極作用。自然,為瞭滿足統治者的貪欲,驛傳有時也不免成為一種殘民的措施。東漢時令南海獻龍眼、荔枝,十裡一置,五裡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就是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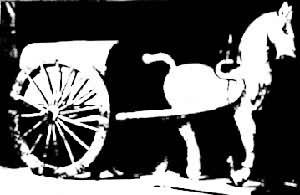 東漢陶馬車 四川成都揚子山出土
東漢陶馬車 四川成都揚子山出土
唐 自三國分裂迄於隋代,驛傳制度缺乏詳細記載。唐代全國空前統一,驛傳的設置,規模超過前代,制度更加完備。全國共置驛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為三十裡置一驛(地勢險阻或須就水草處不限);水驛二百六十所;津渡處置水陸相兼之驛八十六所。陸驛驛馬,京城都亭驛七十五匹,諸道之驛視其繁閑分六等,依次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驛驛船,繁者四隻,次三隻,再次二隻。其驛夫(水驛稱水夫)征取民戶承役,凡三馬給丁一人,一船給丁三人。初,州縣江驛傢中富強者充諸驛驛長,稱為“捉驛”,上元、寶應年間(760~763),始以吏主之。驛馬、車、船由官府提供,諸驛並給錢以市什物、食品。驛館多建在州縣城內,後有遷置城外者;館舍有上廳、別廳(或西廳、東廳)以接待不同品級官員住宿,並設有茶、酒等庫。諸州有專項稅錢以給驛傳經費,每年一小稅,總額四十萬貫;三年一大稅,一百五十萬貫。隨近撥給驛田以種植飼料,大抵驛馬一匹給地四十畝,傳遞馬二十畝。給驛的范圍,主要為奉差齎送公文使者、入覲蒞任官員及各種特遣使臣。根據使命緩急,或給驛,或給傳,前者日行六驛,後者四驛,赦書日行十驛。乘驛皆憑驛券傳牒,在京由門下省發遣,在外由留守及諸軍州發遣,濫發有罪。給驛馬數依官品有差,給驛者自一品八匹遞減至七品以下二匹,給傳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馬。其攜帶私物,乘馬不過十斤,乘車不過三十斤,乘船所帶衣糧什物限二百斤。止驛供給食宿,不得超過三日;五品以上官員私行,許投驛止宿,但不享受飲食。驛傳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駕部郎中負責,諸道各設館驛巡官四人以及判官專知其事,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諸縣令兼理。開元中,命禦史出使就便校察驛傳。後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諸道館驛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館驛使。大歷十四年(779),定監察禦史一人兼館驛使,往來巡察。但後來又有以官充館驛者。唐中後期,由於給驛頻繁,乘驛官員多違制騎乘及索要飲食、饋獻,加以經費不足,以致驛夫困苦、驛馬死損缺額、館舍破敗現象越來越嚴重。
宋 宋代驛傳制度大致沿襲唐代而又有較大發展。驛道四通八達,郊野都鄙之間,二十裡有歇馬亭,六十裡有館,水行州縣有水驛,需持驛券。驛券由樞密院發給,稱“走馬頭子”或“遞馬頭子”。太平興國三年(978)一度取消驛券,改用銀牌;端拱二年(989)復舊。初,內外官員乘驛給馬數缺乏統一規定。嘉祐四年(1059),三司使張方平始據舊例和有關宣敕令文纂集刪改,編為驛券則例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頒行全國。
傳遞文書則有遞鋪,每十八裡或二十裡、二十五裡置一鋪。遞鋪有步遞、馬遞、急腳遞(又稱急遞鋪)和金字牌急腳遞之別,南宋復有斥堠鋪和擺鋪。各種遞鋪傳送文書種類和日行途程不同。皇祐元年(1049)規定,馬遞晝夜行四百裡,急腳遞五百裡。金字牌急腳遞始設於宋神宗時,牌長尺餘,木制,朱漆刻金字,曰“禦前文字不得入鋪”,“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日行五百裡,不以晝夜,鳴鈴走遞,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規定: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裡;事幹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腳遞,日行四百裡;如無急腳遞,其要速並盜賊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裡;常程文書入步遞,日行二百裡。其中遞送赦降的“馬遞”,即指金字牌急腳遞。斥堠鋪和擺鋪也是急腳遞的一種,前者始建於建炎三年(1129),“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十裡置一鋪,每鋪限三刻承傳。後者亦高宗時所置,本為“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設,因其要求經由州軍並取便路互相聯結置鋪,故名擺鋪。初以三十裡、二十裡置一鋪,後改為九或十裡一鋪,日行三百五十裡。除禦前之朱漆金牌外,樞密院給發軍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黃青字牌,沿邊州軍並諸軍統制司申奏軍期急切文字,則有黑漆白粉牌,均創於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三百五十裡。淳熙二年(1175),尚書省遣發急切不可待時文字,亦用雌黃青字牌。紹熙四年(1193),雌黃青字牌改為黑漆紅字牌,期限減作日行三百裡。
入遞的文書又稱遞角。除“禦前不入鋪”文書徑由入內內侍省發遞外,其餘文書的收發均需經過進奏院。進奏院元豐改制後隸門下後省,其任務迄為“掌受詔敕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並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禦、分授諸司”。交付急腳馬遞鋪的文書均需當官實封、不題事目,隻排字號並題寫遣發官司和期限日時,用印以蠟固護,裝入筒內。筒有皮筒、竹筒和紙筒三種。登記遞角入鋪時刻和件數的簿歷分大歷和小歷,大歷是存於各鋪的底簿,小歷由鋪兵隨身攜帶,交接時由下鋪批註回鋪時刻。除官府文書外,雍熙二年(985)還規定允許私書附遞,從而使私書附遞成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驛傳制度的顯著特點。
遞鋪雖以傳遞官府文書為主,但接待使客,運送官物,乃至提供馬匹車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於遞鋪組織的完善和普遍,驛館相對衰落,其職能遂為遞鋪所取代,或與遞鋪交織不可分。
主管驛遞的機構,元豐改制前,中央主要是樞密院,改制後則由尚書兵部之駕部掌其事,但樞密院之教閱房仍負有“催督驛遞”之責。在地方,路一級由轉運使一員提舉,以“提舉××路馬遞鋪”系銜,另設巡轄使臣,每千裡或兩州一人,巡回檢察;其下,州由通判點檢,縣由縣尉、知縣催促。驛遞的服役者,北宋建國伊始,即於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廂兵代百姓為遞夫。這是有宋一代的定制,亦為驛遞制度的一大變革。遞鋪鋪兵,要路每鋪十或十二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腳馬遞輔兵每二十人補節級一名,五百人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往來催趕遞角官物”。
遼金 遼有軍國重事(如抽發兵馬),遣使傳旨,用銀牌(鍍金),長一尺,上刻契丹字,文為“宜速”及“敕走馬牌”,由皇帝親授與使者帶在項上馳驛,並手劄給驛馬若幹匹,驛馬缺則取他馬代,最快一晝夜行七百裡,其次五百裡。銀牌使者所至,如皇帝親臨,需索物品、更易(驛馬),無敢違抗。使回納還銀牌,也由皇帝親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長牌,亦銀質鍍金,由南內司收掌,遣使赴諸道取索物色及進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於遣使往女真、韃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發兵馬,均帶在腰間左邊走馬(馳驛)。據宋人使遼行記和《武經總要》記載,設有從白溝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缽的驛道,宋使入遼即行此道,還有從中京至東京的驛道。兩驛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裡至一百餘裡不等,其間設有中頓,供使客午餐。初,諸縣人民承擔驛遞、馬牛之役,至遼末,始使民出錢,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會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裡置一驛,又令置驛於上京至春州、泰州。後諸路並置。給驛用牌符。乘驛者按官品規定其隨從人數、給馬數和飲食錢數,從一品以上隨從八人、馬十匹、食錢三貫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隨從一人、馬二匹、錢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遞鋪轉送文牒,十裡一鋪,每鋪設鋪頭一人、鋪兵三人,從所轄軍射糧軍內差充。凡元帥府、六部支移,憑勅遞、省遞牌子入遞、日行三百裡。
元 元代驛傳又稱“站赤”,為蒙古語╬amuči的音譯。站,╬am 的音譯(最初曾音譯為“蘸”),即漢語“驛”的意思,元代漢文文獻中有時兼用漢、蒙語,作“站驛”或“驛站”;站赤,意為司驛者,元代漢文文獻中除用於稱站官和站戶外,還混用於稱驛站。
成吉思汗時即仿效中原的驛傳制度,在境內設立驛站。窩闊臺即位後,又命各千戶從所管百姓中簽發站赤、兀剌赤(ulaḥači,馬夫)承當站役,出備馬、牛、車具等物,選地立站;增設瞭從蒙古本土通往察合臺和拔都封地、從國都和林通到中原漢地的驛站;頒佈瞭乘驛的規定等。元朝建立後,全國遍設驛站,據至順二年(1331)成書的《經世大典》記載,總數達一千五百多處(不包括西北諸汗國的驛站在內),構成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網。驛路東北通到奴兒幹之地(今黑龍江口一帶),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葉尼塞河上遊),西南通到烏思藏宣慰司轄境(今西藏地區),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驛站分陸站和水站,陸站又有馬站、牛站、車站、轎站、步站之分;遼東黑龍江下遊地區則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於冰上,運載使者、貨物往來。至元二十六年(1289),為瞭運送外國使臣進貢的奇異貨物,特設從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罷。陸站兩站之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裡至百數十裡不等;如相距路程較長,則於中間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當役站戶和所備馬、牛、舟、車數目,視其交通繁閑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戶多至兩三千戶,一般為百餘戶至數百戶,江南轎站則隻有一二十戶。步站置搬運夫,專為運送貨物而設。
管理站赤的中央機構,世祖初年為中書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後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漢地驛站事屬中書兵部,通政院隻管蒙古驛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統一掌管全國驛站。地方管理體制也幾次變化。初,各地驛站由本處府、州、司、縣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達魯花赤、總管親自提調站赤。十一年定制,各站皆直隸於路,革去州縣一級的管理,其站戶傢屬依軍戶、奧魯例仍屬原籍州縣管領。至大元年,離路城遠的驛站復命當地州縣長官就近提調;延祐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轄,州縣官不得幹預。提調長官要時常檢查所轄各站,督責站官人等勤慎奉職,務令人馬、舟車、館舍、飲食——完備。各站設置站官,稱驛令、提領。大站設驛令一二人,提領二三人;小站一般隻設提領。驛令以雜職人員擔任,受敕,頒給俸祿;提領由地方提調長官從本處站戶中選任,隻受部劄,即充本人身役,不給俸。江南地區的驛站,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漢人一名任提領,給俸;另選本處站戶一名為副使。此外,每一百戶站戶設百戶一名,每站設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現役站戶承當。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樞紐處的驛站設脫脫禾孫(檢查官),專職稽察過往使臣真偽及人員、物品是否違反乘驛規定,因此這些站又稱為脫脫禾孫站。
乘驛憑證有圓牌、鋪馬聖旨和劄子。圓牌也稱圓符,按規定專為軍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鑄造、掌管(掌管部門為典瑞院),諸王公主駙馬及出征、守邊軍帥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頒給若幹面,以備隨時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圓牌乘驛,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銀字圓牌。初,圓牌上鑄有海東青圖像,因稱海青圓牌;至元七年改換牌面,不用海東青,改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據現存圓牌實物,牌面文字漢譯為:“長生天氣力裡皇帝聖旨:違者治罪。”佩帶圓牌的使者,有擇騎良馬、兼程馳驛、馬乏時可以奪騎官民馬匹等特權。一般公事差遣人員,皆給以鋪馬聖旨乘驛。鋪馬聖旨也稱禦寶聖旨,用蒙古文字書寫,每道聖旨上都分別標明起馬數目,從一匹至十幾匹不等;通常經由中書省奏準,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並填寫領受官府名稱,以限定在職責范圍內使用。各官府領取的圓牌和鋪馬聖旨,由擔任長官的蒙古人掌管、遣發。元初,中書省、樞密院、禦史臺及行省、行臺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鋪馬劄子給驛;至元十九年定制,一律憑鋪馬聖旨乘驛,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僅經行水站者不用聖旨,仍從中書省出給船劄。此外,諸王也可以自發鋪馬令旨給驛,但他們濫發令旨遣使,嚴重擾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終未能禁絕。諸官府以圓牌或鋪馬聖旨遣使,一般需隨附差劄(或稱印信文字、別裡哥文字),開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隨從員數、起馬數目等項。站官驗看圓牌、聖旨和差劄後,方能應付鋪馬、飲食。使者應按其使命由規定的驛路行走,不得繞道馳驛、乘機探親訪友或遊玩,公事完畢,即將所領乘驛憑證納還原發官司,不得稽留。乘驛人員應給的馬、舟、車數目,視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飲食分例(元代文獻中常稱為“首思”,系蒙古語šiḥüsün的音譯)也有規定:在驛館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鹽雜鈔三十文,隨從隻給米、面;過路者減半。冬月每日另給炭五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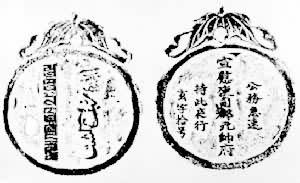 元站赤腰牌
元站赤腰牌
元代驛傳的弊端更甚於前代。泛濫給驛的情況一直非常嚴重,圓牌常被用於非軍務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獵、采辦珠寶異物等,甚至發給斡脫商人往來貿易;諸王貴族官吏更常以鋪馬聖旨、令旨差人乘驛辦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勢勒索站戶,多取鋪馬、飲食;或違制急馳,超重馱載,以致損傷車馬,卻逼令站戶補置。政府常不按時發下祗應官錢,至有連續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戶輪當庫子(負責供應物資的驛站司吏)賠辦供應;加以管站官吏聚斂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貧難站戶賣妻鬻子以應役。這些都造成站戶逃亡,鋪馬短缺,驛傳制度因而日益衰敗。
傳送公文的郵驛,稱急遞鋪(簡稱遞鋪),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統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開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遞鋪,每十裡或十五裡、二十五裡設一鋪,每鋪置鋪兵五人,於各州縣取不能負擔差發的貧戶及漏籍戶充役,免其差發。不久即令各州縣依例設置,與鄰境所置鋪相接,路府州縣委正官一人提調。至元三十一年(1294),於大都置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設提領三員;各路置總鋪,設提領一員。至治三年(1323),又於每十鋪置一郵長。初定中書省、六部、禦史臺、樞密院及各行省、行臺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許入遞,其後擴大入遞范圍,凡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官府來往公文均可入遞。傳遞辦法:省、臺、院及邊關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用黑油紅字書寫號碼,並標明發送、承受衙門及入遞時刻,隨到隨送。一般公文皆付承發司,按所投下處分類裝封,每件系一牌,用綠油黃字書寫號碼,交鋪傳遞。各鋪收到入遞公文,由鋪司(鋪兵頭目)於鋪歷上登記文目及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即令鋪兵裝裹停當,隨帶回歷一本,急速送遞至前鋪交割;前鋪鋪司驗收後於回歷上簽押,付來人持回,隨交本鋪兵送往下一鋪。如此依次傳遞至目的地,一晝夜需行四百裡,急件五百裡。鋪兵腰系銅鈴、持槍、挾雨衣,夜則持火炬,沿途其他人聞鈴應為讓路。除大都、上都間可遞送禦膳菜果外,其餘急遞鋪隻遞公文,不許將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冊入遞。
明 明代驛傳機構,在京城設會同館,地方分別設水馬驛、遞運所和急遞鋪。
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正統六年(1441),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在北京;南館三所,在南京。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總轄館務。內以副使一員,分轄南館。弘治(1488~1505)中,添設禮部主客司主事一員,專一提督。凡各王府差遣人員、遼東建州等衛、西北諸國使臣及雲貴四川湖廣土官番人等,俱於北館安頓。瓦剌、朝鮮、日本、安南等國進貢使臣,俱於南館安頓。館夫額設四百名,南館一百名,北館三百名。
① 水馬驛。兩京十三佈政司共設水馬驛一千處以上。馬驛六十裡或八十裡一置,沖要去處,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不等,其餘亦設馬二十匹、十匹,以至五匹。各驛馬匹分上、中、下三等,馬膊上懸掛小牌,明寫等第。馬夫備有銅鈴,遇有緊急公務,懸鈴身上,前路驛聽候鈴聲,隨即供應,不致妨誤。水驛設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驛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每船設水夫十名。
② 遞運所。在陸路者設置車輛,大車能載米十石者,每車人夫三名,牛三頭,佈袋十餘。小車人夫一名,牛一頭。在水路者設置船隻,船俱用紅油刷飾,每船置牌一面,開寫本船字號、料數、水夫姓名及檣、柁等一應浮動什物數目,以供點視。六百料者,每隻水夫十三名;五百料者,每隻十二名;四百料者,每隻十一名;三百料者,每隻十名。遞運所或置或革,時有變動,據萬歷會典的統計,尚有一百四十餘處。
③ 急遞鋪。每十裡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四名,專一傳送公文。每鋪設日晷一個,以驗時刻。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裡。公文到鋪,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齎小回歷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歷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
 明弘治年間驛馬符驗
明弘治年間驛馬符驗
乘驛需憑符驗。傳送文書亦須蓋有印信,以防作偽,這種印信為加蓋騎縫半印,以憑板勘對合,故稱“勘合”。
應合給驛的范圍,主要有:①齎擎訟旨及奉旨差遣給驛者。②飛報軍情重事者。③親王進表奉賀及差人奏事者。④各藩屬使臣之進貢及回國者。⑤文武官員到任在一千五百裡以外者。⑥職官病故,其屍體及傢屬回鄉者。另外,孔子後裔也享有給驛待遇。
驛傳夫役,由各地州縣,按照配定的名額,在本地糧戶內僉編應役。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上馬一匹僉編民戶納糧在一百石以上者備馬到站應役,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水夫由民戶納糧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者充當;急遞鋪鋪兵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鬥以上二石以下者充當。一戶糧額不足,允許眾戶合糧湊足一夫,稱“朋編”;當地糧額不足編僉,可由同府其他州縣僉夫協充,稱“協濟”。嘉靖年間,驛傳夫役計糧折銀正式實行,稱“站銀”,由官府雇役承當。
驛遞的管理,掌於兵部車駕清吏司,在地方則由佈政、按察二司共同負責。對違制者規定瞭處罰條例。
清 清代驛傳,以京城皇華驛為中心,通達全國。各省所設稱驛,屬所在廳州縣兼管,間有設驛丞專管者;盛京所設亦稱驛,專設驛丞管理,不隸州縣。通達西北邊疆軍報所設者稱站(自京城回龍觀站而西,分兩道,一至張傢口,接阿爾泰軍臺,一往山西、陜西、甘肅出嘉峪關,接安西州軍塘);吉林、黑龍江所設亦稱站,統於吉、黑將軍;自喜峰、古北、獨石、殺虎四口分道達於內蒙古各旗,亦設站(蒙旗境內為蒙古站),於四口各派理藩院章京統之。西北兩路所設者稱軍臺,分隸於阿爾泰軍臺都統、烏裡雅蘇臺將軍、科佈多大臣、庫倫大臣、伊犁將軍及新疆諸城大臣。安西、鎮西、哈密所屬特設軍塘以通軍報,設營塘以通尋常文報。計全國(除西藏外)所設驛、站、臺、塘共兩千餘處,統稱驛站。
清初亦置遞運所,後並歸驛站,惟甘肅一帶猶存其制,各設牛馬專司運載。各省皆設鋪司,各以鋪夫、鋪兵走遞公文。
各站驛夫,經行大路每站設一二百名或七八十名,偏僻小路二三十名,兵部會同館(皇華驛)四百名。驛夫工食每日給銀二三分至七八分不等,由驛站錢糧內開銷。蒙古站及西北兩路軍臺,則由蒙古各旗及新疆各部、各城人民供役。
各站驛馬、驢、牛皆有定額,會同館六百九十匹,其餘視沖要或偏僻,自百餘匹至一二十匹不等,並按各地道路險易規定每年的折損(倒斃)比例。驛車及水站驛船則規定瞭大、小修和拆造年限。
驛站仍歸兵部總管。凡應給驛者,發給郵符為驗,稱勘合、火牌,其往來應供馬匹、廩給及跟役人數、口糧,按品級為等差,皆於勘合上填註。驛遞則驗以火票,定其遲速之限(自日行三百裡至六百裡),按所達之路程計其時日。鋪遞亦同。對驛站馬匹車船廩給有缺,遞送公文遲誤失損,馳驛者多要馬匹廩給、多帶跟役、行李或枉道馳驛,入遞文冊物品夾帶私物等情,都規定瞭治罪條例。但違例之事時有發生,特別是奉差馳驛官員騷擾、諸官司泛濫交遞及州縣官貪污克扣驛站錢糧,以致夫馬疲敝缺損,驛遞遲誤嚴重,雖屢令整治,迄無成效。咸豐間,馮桂芬力陳驛站積弊,建議裁減,效西法設郵政局。咸豐、同治以後,隨著輪船、鐵路、電訊、郵政相繼發展,驛站逐漸變得無足輕重。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始特立郵傳部以掌輪、路、電、郵,在此前後,驛站相繼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