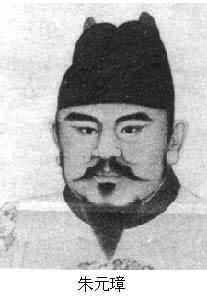 朱元璋
朱元璋
即明太祖,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鐘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餘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瞭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瞭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瞭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主張治亂世,“刑不得不重”,並以此為指導,采取瞭下面一些以“猛”和“嚴”為主要特點的措施:
修訂律令,刑用重典 明代法律草創於洪武建元以前的吳王時期。吳元年(1364),朱元璋就曾指令當時的重要輔佐李善長主持修律,要求作到既簡且嚴,並親自“酌議”,頒有《律令直解》。建國初年,令劉惟謙等詳定《大明律》,經過多次修改刪定,頒行全國,奠定瞭有明一代立法的基礎。明律“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貫徹瞭“刑用重典”的方針。特別是洪武十八年由朱元璋親自采輯吏民犯罪處刑的案例,編纂頒行《明大誥》及其《續編》、《三編》和《大誥武臣》,所列論罪處刑的辦法均極嚴厲。“凡三誥所列凌遲、梟首、種誅(即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並首創對朝廷大臣使用的“廷杖”制度。所有這些規定,在執行上都不稍寬貸。如大將胡大海奉命在浙東打仗,他兒子在京犯瞭酒禁,立即處死,聲稱“寧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渡江舊將趙仲中守安慶,在城陷撤回京都後,朱認為“法不行,無以懲後”,也立即賜弓弦一條令自殺。因為懲罰過多,辦事人手不夠。曾立有帶罪辦事的辦法,如有的被判死刑後戴著腳鐐坐堂問案,有的打瞭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作官之類。這些嚴厲的作法到後期有所改變,如強調“刑用重典”和“法外用刑”是一時的權宜,“本非常典”,治國不能“純任刑罰”,並規定後嗣執法隻準以“律”和“大誥”作根據,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等殘酷的刑罰等等,但峻令實行既久,實際上對社會已經造成瞭嚴重的消極影響。
 明代錦衣衛印
明代錦衣衛印
整肅官風,嚴懲貪吏 洪武初期,即逐步建立瞭比較完備的官吏考課和監督的制度。除頒佈《明大誥》外,還陸續頒行瞭《臣戒錄》、《武臣保身錄》、《皇明祖訓條章》等多種要求諸王和各級官吏遵紀守法的戒律和文告。對犯罪官吏除使用上述凌遲、梟首、種誅等刑罰外,還使用抽腸、剝皮、挑膝蓋等各種非刑。特別對於貪官污吏,更是加重懲辦。即位之初,便將官吏貪污犯笞罪以上的,一律押到鳳陽屯田,一時多達1萬多人。後來更是隨犯隨殺。地方上的守、令貪污,準許老百姓赴京城告狀。凡犯贓銀六十兩以上貪污罪的,都在各該衙門左側場地上的“皮場廟”前剝皮,然後在皮裡填充稻草,置於大堂公案旁,用來警戒繼任官吏。又曾多次組織全國范圍的對貪官污吏的甄別和清洗,每次逮捕處死的人達數百以至成千上萬之多。洪武十五年發生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發生的郭桓貪污案,被株連殺戮的先後達好幾萬人。由於誅戮范圍大、牽涉廣、人數多、刑罰重,曾在官僚中長期造成恐怖氣氛,人人朝不保夕,不少人凌晨離傢上朝時,即和妻子訣別,吩咐後事。所謂“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這種作法,原本出於“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但事實上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徒使“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傢誅戮者多”而已。
令行禁止,不避親貴 洪武初年,文武勛臣居功自傲、驕恣不法的現象迅速發展,有無法禁戢之勢,危害到朱明王朝的根本利益。為瞭嚴肅法紀,加強統治集團內部的約束,特於洪武六年命令工部制造鐵榜一種,上鑄申誡公侯的命令,列舉犯罪情狀,逐條規定罰則。凡公侯傢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產財物,和私托門下隱蔽差徭的,都處斬刑。同時鑒於歷史上宦官、外戚為禍的教訓,建國不久即立下規矩,凡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許幹預政事,不許兼外朝職銜,甚至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內廷官級不許超過四品等等;並規定外朝各衙也不許和內官有公文往來。對外戚幹政的預防,則是禁止後妃參預政事。凡違犯這些規定的,大都也要處死。不死的也要受到嚴厲懲辦,令行禁止,無論親疏貴賤,一律不稍寬貸。如開國勛臣朱亮祖位在公侯,權勢很重。出鎮廣東時收受賄賂,枉法縱囚,並誣告番禺知縣道同致死。事發後,朱和他兒子朱暹都被鞭死。又安慶公主的丈夫、駙馬都尉歐陽倫,在茶禁正嚴時,派遣傢奴販運私茶,並縱容傢奴周保妄作威福,肆意指揮和凌辱地方官。事發後賜歐陽倫死。並未因為他是自己的女婿而予以寬貸。這些作法對加強洪武年間封建法制的威力,有重要的作用。
任用特務,濫肆誅戮 為瞭鎮壓不斷興起的人民反抗和進行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洪武年間曾制造許多大案,濫肆誅戮。如設置檢校組成的嚴密的特務網,執行察聽、偵伺的任務。胡惟庸謀反案發後,洪武十五年又以護衛皇宮的親軍為基礎,設立瞭名為錦衣衛的特務機構。它由皇帝指揮,專掌侍衛、緝捕和刑獄,被授權審處全國所有重要的政治性案件,直接取旨行事;曾借偵察所謂“不軌、妖言”案件,大興“詔獄”,拷訊慘烈,在丞相胡惟庸和太子太傅藍玉謀反兩案中,胡案被株連殺戮達三萬多人,藍案被株連殺戮達一萬五千多人。這些誅戮加上文字獄和別事肆行誅戮的結果,致“諸功臣宿將殆盡”,“文臣亦多冤死”。這種局面的造成,雖然不能完全歸之於他個人的“猜忌好殺”,同時後期他也有所改變,如先後焚毀錦衣衛刑具和規定內外刑獄公事不再經由錦衣衛,仍由朝廷法司處理,又指出他這是“治亂世”所采取的措施,不要後嗣效法之類,但盡管有所改變,也已造成瞭嚴重的危害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