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北方遊牧部族。又稱胡。其名始見於戰國文獻。起源不明,或以為即周代典籍中所見狁、薰粥之後。其族屬和語言系屬有蒙古、突厥、伊朗諸說,迄今尚無定論。匈奴人沒有文字,以言語為約束。
 匈奴人三馬形銅飾牌 內蒙古察右後旗二蘭虎溝出土
匈奴人三馬形銅飾牌 內蒙古察右後旗二蘭虎溝出土
政治組織與社會經濟 匈奴人以畜牧為主,畜有羊、牛、馬、騾、驢和駱駝等。馬最受重視,為戰鬥、運輸、貿易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畜產歸私人所有,各部落牧地則為各該部落牧民所共有。匈奴人住氈帳(古曰穹廬),食肉、飲乳及馬乳酒,衣皮革,過著逐水草遷徙的生活。匈奴貴族亦居住漢式宮殿,這些宮殿可能成於漢工匠之手。匈奴人會建造軍用的壁壘、城堡等;有車、船,能築路、架橋。匈奴冶銅業發達,能鑄刀、劍、斧、鏃和馬具等;冶鐵和制陶也有一定的規模。
匈奴的社會組織以部落聯盟為主,聯盟的首領稱為“單於”。公元前3世紀末以後,匈奴征服鄰近各族,統一蒙古高原,遊牧的國傢政權機構逐步形成。單於以下,高級官吏依次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等,主管軍政,均由單於子弟、本部落貴族擔任,皆世襲。此外,有左、右骨都侯等,輔佐政務、斷獄聽訟,一般由異姓貴族擔任。
匈奴由許多部落構成,各部落包含若幹氏族,著名的如孿毬氏、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韓氏、郎氏等。孿毬氏最貴,單於皆出此族。或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其餘有呼衍、蘭、須卜、丘林四族亦貴,世與單於聯姻。凡廢立、和戰、祭祀等大事,均由各部貴人會議決定。
匈奴有不成文法,盜竊者沒其財產,大罪死,小罪軋;監禁最長不出十天,一國的囚犯不超過十人。
匈奴人朝拜日,夕拜月;月滿進軍,月缺退兵;戰場上能斬得敵首的,賜酒一杯。凡有掠獲,皆歸己有,以俘虜為奴婢。打仗時能運回死者屍體的,可得死者全部傢財。匈奴絕大部分是騎兵,男子少壯能挽弓者均在編內。
匈奴行族外婚;父兄死,妻後母,報寡嫂。匈奴人土葬,死者頭部朝東。貴族皆深葬,棺祔多達三重。單於死,金銀、衣裘隨葬之外,近幸臣妾從死者多達數十百人。
匈奴於每年正月,小會單於庭,祭祠。五月,大會龍城(今蒙古鄂爾渾河西側和碩柴達木湖附近),祭祖先、天地、鬼神。秋日馬肥,大會蹛林,檢點人畜。南匈奴降漢後,仍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秦及漢初時期 秦初,匈奴分佈在陰山南北地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蒙恬率軍三十萬往擊,奪取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一帶),重置九原郡(治今內蒙古包頭市西),連接秦、趙、燕舊日長城並重加修築,西起臨洮(今甘肅鎮原南),東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三十六年,又遷三萬戶墾殖北河(今內蒙古杭錦旗一帶)、榆中(今河套東部),以防匈奴南下入侵。
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頭曼單於乘中原動蕩之機,收復河南地;至其子冒頓單於(?~前174)殺父自立時,匈奴已有控弦之士三十萬,遂西破月氏,東擊東胡,北服丁零,南並樓煩、白羊;並乘楚漢相爭之隙,屢犯燕(今河北北部)、代(今河北蔚縣一帶)。
漢高帝七年(前200),匈奴兵圍馬邑(今山西朔縣),南擾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漢高祖劉邦親率軍三十餘萬出擊,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遇伏被困,不得已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以公主嫁單於,歲奉貢獻,並開關市與交易。
約前177或前176年,匈奴西進,再次擊敗月氏,迫使月氏向西北潰退至伊犁河流域;接著又征服烏孫、呼揭,以及樓蘭等塔裡木盆地綠洲諸小國。其西部日逐王在西域北道焉耆、危須與尉犁之間置“僮仆都尉”,控制商道,榨取財富。老上單於在位(約前174~前160年間)時,又大敗月氏,殺其王,以其頭為飲器。此後(約前139~前129年間),匈奴又令烏孫進攻月氏,月氏再西遷至媯水(今阿姆河)流域,烏孫遂據有伊犁河流域。
匈奴與漢雖結和親,然恃其強盛,仍不斷侵擾長城以南地區,匈奴騎兵曾一度燒毀回中宮(在今陜西隴縣),前鋒直指長安甘泉(在今陜西淳化西北)。
漢武帝至王莽時期 西漢王朝經過六十餘年休養生息,國力漸充,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便立志北伐。元光六年(前129),漢兵自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代郡、雲中(今內蒙古和林格爾)、雁門(今山西右玉西北)四道並出,擊匈奴於長城下。元朔二年(前127),漢將衛青取河套以南,置朔方(今內蒙古杭錦旗北)、五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北)二郡,徙民十萬以實之。元狩二年(前121),漢將霍去病出隴西,攻克焉支(今甘肅永昌西、山丹東南)、祁連二山;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眾四萬餘歸漢,漢在兩王故地先後設酒泉(今甘肅酒泉)、武威(今甘肅民勤東北)、張掖(今甘肅張掖西北)、敦煌(今甘肅敦煌西)四郡;從此自河西走廊至羅佈泊一帶無匈奴,匈奴與西羌的聯系斷絕。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率步、騎兵數十萬分兩道並出,夾擊匈奴於漠北。漢軍大勝,封狼居胥山而還。同時,武帝遣張騫等出使西域,約結月氏、聯姻烏孫,力圖斷匈奴右臂。嗣後,匈奴與漢反復爭奪西域門戶樓蘭、車師等地,前後凡二十餘年。宣帝本始元年(前73),匈奴擊烏孫不利,衰兆已現。丁零、烏孫、烏桓等各乘虛攻擊,其勢益弱。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漢,漢得車師,西域始暢通;漢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西域諸國多屬都護管轄,從此匈奴僮仆都尉不復存在。
不久,匈奴統治集團內訌,五單於爭立。宣帝五鳳元年(前57),終於分裂為東、西兩部。東部呼韓邪單於於甘露三年(前51)降漢,覲見漢宣帝劉詢。西部郅支單於西遷至康居住地,役使近旁烏孫、呼揭、丁零諸小國;元帝建昭三年(前36)被漢將陳湯等擊殺於楚河上。郅支既滅,呼韓邪於竟寧元年(前33)再次朝漢。元帝以後宮良傢子王嬙(昭君)嫁呼韓邪,號“寧胡閼氏”。從此匈奴不斷朝漢,並遣子入侍,和平相處凡四十餘年。王莽執政,降低對單於的待遇,阻止烏桓等向匈奴納稅,於是匈奴重又入侵。一度北邊空虛,不斷為匈奴所蹂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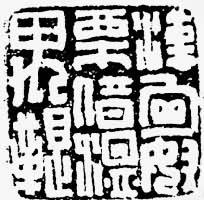 漢朝賜給匈奴王溫禺鞮的“漢匈奴栗借溫禺鞮”銅印 內蒙古伊克昭盟東勝征集
漢朝賜給匈奴王溫禺鞮的“漢匈奴栗借溫禺鞮”銅印 內蒙古伊克昭盟東勝征集
東漢、魏晉時期 光武帝之初,漢與匈奴關系仍未好轉。後因塞北連遭饑旱,又受烏桓等攻擊,匈奴疲憊已極,內訌又起,日逐王比於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自立,亦號呼韓邪單於,率漠南八部歸降於漢。匈奴遂分裂為南北兩部。
南匈奴部眾駐牧於漢北邊五原、雲中、定襄(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朔方、雁門、上谷、代、北地(治今甘肅慶陽西北)八郡之內;漢對於南匈奴歲賜豐厚,且於建武二十六年設“使匈奴中郎將”以監護之。明帝以後,更設度遼營於五原曼柏(今內蒙古達拉特旗),置度遼將軍,協助南匈奴單於抵抗北匈奴來侵和鎮壓族人的叛亂。此後,南匈奴或降或叛,然節節南徙。至2世紀40年代多數集中於並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帶。東漢末,曹操怕匈奴勢力蔓延,始限制其居住地區,分其部眾為左、右、南、北、中五部,並采取分化政策,使上層貴族與部眾脫離。此後南匈奴單於僅有虛名,王侯降同編戶,部分匈奴牧民逐步淪為漢族地主的農奴。西晉末,匈奴屠各氏貴族劉淵趁八王之亂據有並州,建立“漢”政權,後其族子劉曜為帝時,改國號為“趙”,前後立國二十六年(304~329)。東晉末,鐵弗匈奴赫連勃勃建立“夏[ID=xia_shiliuguo]”政權,立國二十五年而亡(407~431)。南北朝後期,匈奴之名逐漸消失。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將竇固、耿忠出酒泉塞,擊敗北匈奴呼衍王,追蹤直至蒲類海(今新疆巴裡坤湖),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今新疆哈密)。次年,竇固、耿忠又合兵擊平車師前、後王,重置西域都護,切斷北匈奴同西域的聯系。北匈奴困窘,諸部南下歸漢者逐年增多。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漢將竇憲、耿秉等得南匈奴之助,又大敗北匈奴,逐北三千裡,登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記功而還。永元二年、三年,漢軍又連續大破匈奴,斬獲甚眾,單於遁逃,漢軍出塞五千裡始還。此後,由於鮮卑興起,占有匈奴故地,北匈奴部分投漢,部分歸降鮮卑。其餘殘眾或降或叛,出沒於天山南北,繼續與漢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屢為邊患。其蹤跡直至2世紀中葉才不見於記載。或以為歐洲史上的匈人(Huns)即西遷的北匈奴,但未有確證。
近年來,從匈奴貴族墓中出土瞭不少青銅器,如兵器、馬具等,上面的動物紋飾高度寫實,栩栩如生,與中亞、南俄等地遊牧部族中流行者相類似,或以為這是匈奴人同自西向東擴展的斯基泰(Scythai)文化相接觸的結果。另外,通過戰爭、和親和關市,匈奴大量地接受瞭漢文化的影響。匈奴人墓葬中有許多漢式絲綢服裝、銅鏡、馬具、漆器等,均是明證。同時,漢經濟文化也受惠於匈奴,當時養馬業的發達,就與匈奴馬匹的輸入有關,騎兵的訓練與有關戰術的進步也受到匈奴的影響,足見匈奴在東西經濟、文化交流中起過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