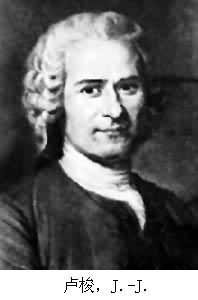 J.-J.盧梭
J.-J.盧梭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傢、哲學傢、社會政治思想傢和文學傢。1712年6月28日生於瑞士日內瓦。父親是個鐘錶匠。盧梭10歲時,父親和人發生糾紛敗訴,逃往裡昂,把盧梭託付給他舅父。此後盧梭從事過多種職業,學“承攬訴訟人人”,當鐘表行業學徒,直至1728年3月14日因不堪虐待逃出日內瓦投奔華倫夫人。1742年7月,盧梭隨身攜帶一部《新記譜法》離開華倫夫人前往巴黎,在法蘭西學術院宣讀,未獲認可。在此期間,他先後結識瞭É.B.de孔狄亞克、D.狄德羅、J.L.R.達朗貝爾和格裡姆萊等人。1743~1744年,盧梭給法國駐威尼斯大使M.de蒙太居當秘書,隨後返回巴黎。1750年,發表《論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否有助於敦風化俗》。1755年4月,發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6年4月,盧梭因厭倦巴黎生活避居離巴黎不遠、鄰近蒙莫朗西的“退隱廬”。其後6年,他構思、寫作瞭《社會契約論》、《愛彌爾》、《新愛洛伊絲》和《感性倫理學或智者的唯物主義》綱要,他為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寫的條目《論政治經濟學》也在這段期間出瞭單行本。1762年6月,法國政教當局下令禁止《愛彌兒》和逮捕盧梭,盧梭匆匆逃出巴黎,先到伯爾尼,進而輾轉避居普魯士的訥沙泰爾邦莫蒂埃村。1764年底,盧梭收到一本對他進行刻毒的人身攻擊的匿名小冊子《公民們的感想》,他本已深受迫害,遂萌發瞭寫作《懺悔錄》的念頭。翌年9月,又出奔聖·皮埃爾島,被逐,又前往英國,受到D.休謨的友好接待。1767年5月,盧梭懷疑休謨參與瞭迫害他的陰謀,逃回法國,在法國各地輾轉數年後,於1770年重返巴黎。此後直至臨終,盧梭基本上隻寫作瞭一些自我辯護和回憶錄性質的作品。1778年5月,移居埃爾姆農維爾,7月逝世。
盧梭思想的基本特征 盧梭的著述生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獨創性。與盧梭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傢們都歌頌科學和藝術、理性和規律、知識和邏輯、文明和進步,用理性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相信理性的進步將自然而然導致人和社會的完善。盧梭則把自然和文明尖銳對立起來,並為回復自然大聲疾呼。他所理解的自然,是指不為社會和環境所歪曲、不受習俗和偏見支配的人性,即人與生俱來的自由、平等、純樸、良知和善。盧梭認為,現存的人是壞的,但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假如能為人造就新的、適合人性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教育,人類就能在更高階段回復自然。正是這一基本論點構成盧梭全部思想的出發點和發展線索,他的社會政治學說、認識論、倫理學、自然宗教和自然教育的思想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抽象人性論是形而上學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學說,它撇開歷史的實際運動,而把邏輯上的首尾一致放在首位。但盧梭所說的自然與其說是在歷史的特定時刻曾實際存在過的狀態,不如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批判尺度。它既有力地批駁瞭基督教的原罪說,又使現存社會的弊端顯得格外觸目。因此說,盧梭與啟蒙運動的總潮流又殊途同歸,這也是盧梭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之一。
認識論和宗教觀 盧梭這兩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愛彌爾》第4卷“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由”中。他的認識論受孔狄亞克的影響很大。他認為,感覺是認識的唯一源泉,感覺的產生與消滅是主體不能決定的,因而感覺與感覺的對象不是同一個東西,外在於主體並對感官發生作用的是物質。在他看來,感覺比判斷、推理可靠,因為它更直接,更少主觀成分,更接近自然,人的意識、感情和行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感覺的影響,然而不是消極的感受而是能動的思維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他認為,真理是客觀的,認識越符合對象就越接近真理。
盧梭指出,宇宙的永恒運動和普遍和諧,表明存在著有意志、全能和智慧的上帝,但上帝並不幹預人的行為領域,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是使人棄惡從善的道德基礎。隻要有助於實現這一目的,崇拜何種神、教條和教規的差異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崇拜應發自真誠、自然的感情。他認為,宗教爭執和迫害是無意義的惡行,信仰應該是自由的,各種宗教應互相寬容。
社會政治學說 《社會契約論》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愛彌爾》篇首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瞭人的手裡,就全變壞瞭”。探索這種變化的緣由和發展,制訂完善社會政治制度的方案,是盧梭社會政治學說的基本內容。
盧梭議為,人類在組成社會,建立國傢前,曾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當時人人自由、平等,既沒有政治奴役和剝削,也沒有社會的和精神的不平等,但隨著人類各種機能的發展,生產力的進步,特別是由於私有制的出現,人類通過訂立社會契約建立瞭國傢和法。人類訂立社會契約本是為瞭維護自己的自由、平等、財產和人身,但其後人類的一切社會發展隻是走向與訂立社會契約原意相反的方向。在社會狀態中,文明每前進一步,社會對抗和不平等就加深一步:先是社會契約的訂立確立窮富差別;繼而是權力機構的設置確立強者和弱者的區別;最後是暴君專制的出現確立主人和奴隸的區別。當暴力成瞭暴君的唯一支柱、一切權利和義務都不復存在時,事物的自然進程就是人民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暴君,訂立新的社會契約,重建新的平等。歷史發展經歷瞭各必然階段,不平等的演化完成瞭否定之否定的圓圈。這些觀點表明盧梭的社會歷史觀中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恩格斯曾對此給予高度評價。
盧梭和他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傢一樣,實際上把歷史發展截然劃分為啟蒙前和啟蒙後兩個時期。他認為,人類迄今為止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礎上的。《社會契約論》描述瞭建立合理國傢制度的方案:社會契約應規定人人都同等地把權利轉讓給政治結合體、無例外地遵守契約、同意服從“公意”。“公意”不同於“眾意”,後者是個別意志的機械總和,前者則是“眾意”中相通的部分,即人民的共同意志。國傢應實行法治,法律是“公意”的表現,應由人民來制訂,統治者不能違反法律,否則就必然導致專制暴政。國傢中可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權力的劃分,但後兩者從屬於主權,而主權應永遠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裡。議員和政府不是主權的擁有者,而是受人民委托的。人民不僅有定期決定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利,而且有通過起義推翻暴政的權利。由於盧梭一貫把道德與宗教聯系在一起,他還主張國傢可以制定“公民宗教”,激發公民的自由、愛國情操和犧牲精神。
影響 盧梭的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產生過很大影響。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領袖許多都是盧梭學說的信徒。《人權宣言》許多條文幾乎直接照搬《社會契約論》的原文。國民大會的成立和審判路易十六都援引瞭人民主權論。羅伯斯庇爾對三權分立說的攻擊、他主持的最高主宰崇拜和國民大會的“六月法令”都深刻反映瞭盧梭思想的影響。盧梭的“公意”和自由學說;他在《新愛洛伊絲》中闡發的不能將人單純地用作工具的思想;他將自然和道德劃為兩種不同性質的領域,認為前者受必然律支配,後者受自由律支配;他由意志自由推出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的思想,對I.康德的倫理觀乃至其整個體系的結構都有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