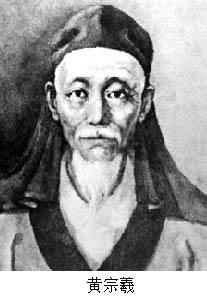 黃宗羲
黃宗羲
中國明清之際的思想傢、哲學傢。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黃竹浦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父黃尊素,明天啟間官至禦史,因與魏忠賢閹黨鬥爭,於天啟四年被捕,死於詔獄。時黃宗羲17歲。崇禎元年,,閹黨遭禁,黃宗羲赴京訟冤,以鐵椎傷仇人宦官許顯純。崇禎十一年(1638),閹黨餘孽阮大鋮在南京圖謀再起,黃宗羲與復社領袖顧杲為首簽署《南都防亂揭》,揭露阮大鋮等人的罪惡。清兵入關後,阮等在南京擁福王監國,對復社進行鎮壓,黃宗羲被捕。清兵攻陷南京,黃宗羲得以逃回傢鄉。時明吏部給事中熊汝霖等舉兵抗清,黃宗羲集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響應,號“黃氏世忠營”。抗清失敗後,感到復明無望,乃隱居傢鄉,總結明亡教訓,著述終生。
黃宗羲學識淵博,對天文、算學、地理等等均有研究,尤長於史學,創浙東史學派,開清代史學研究新風。他一生著作70餘種,1000餘卷,重要的有:《明夷待訪錄》、《易學象數論》、《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南雷文定》、《南雷文案》、《南雷文約》等。
哲學思想 黃宗羲的哲學思想比較復雜。在理氣關系上,他基本上堅持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氣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他說:“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一本也”,“無氣則無理”、“理為氣之理”。他反對程朱理學把理作為獨立存在的實體,說:“世儒分理氣為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墜入佛氏障中。”認為理隻是氣運行變化的條理,隻存在於氣中。在心物關系上,則傾向於王守仁心學,持唯心主義觀點。他說:“人受天之氣以生,隻有一心而已”,“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把氣與心、理與性等同起來,混淆瞭心同氣的原則界限,得出瞭“心即氣”的錯誤結論,把心作為世界的本原,認為“盈天地皆心也”,“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
黃宗羲哲學上的這種深刻矛盾,表明他既已走上瞭沖破理學的道路,卻又無力擺脫理學的羈絆。這是時代對哲學傢影響的結果。
社會政治思想 黃宗羲對中國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和他思想的最精彩之處,是他對封建主義君主專制進行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表現出來的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認為,上古時代,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這種關系被顛倒瞭,“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君主為一人之私,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他認為如此不如無君。黃宗羲在《原臣》中明確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愛樂”,認為君主應該以“天下萬民為事”。在君臣關系上,他嚴厲批判君把臣作為奴仆的隸屬關系,認為君、臣對天下萬民的事,要共同負責。他反對君把臣作為奴仆,也反對臣對君盡愚忠。黃宗羲在《原法》中區別瞭“天下之法”與“一傢之法”,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認為“三代以上之法”是為天下立的,而封建專制主義的“三代以下之法”,隻是為君主“一己而立”,他呼籲廢除“一傢之法”,恢復“天下之法”。
在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基礎上,黃宗羲提出瞭以學校為議政機構的設想。他特別重視學校的作用,認為一切大政方針,都應出於學校。學校應該是決定是非的最高機構,“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黃宗羲所設想的學校,有議政的職能和監督的作用,服從輿論,決定是非,有近似議會的性質。
黃宗羲反對傳統的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的陳舊觀點,明確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
黃宗羲的思想,是明代中葉以後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它體現出明清之際唯物主義思想高漲和出現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特點,而且成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他的《明夷待訪錄》一書,清廷曾列為禁書,但清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曾將它復印、散佈。黃宗羲的思想在中國初期民主運動中起過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