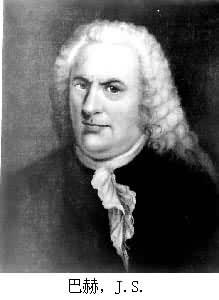 J.S.巴赫
J.S.巴赫
德國作曲傢、管風琴傢。1685年3月21日出生於愛森納赫的世代音樂傢庭,其5代遠祖魏特·巴赫系匈牙利鄉村麵包師,喜愛演奏樂器,篤信路德新教。因當時匈牙利魯道夫二世反對宗教改革,乃遷居德國。此後4代傢族成員多系民間樂樂師、城市吹鼓手或城市管風琴師。巴赫之父J.A.巴赫原為愛爾福特城市吹鼓手,後任愛森納赫城市樂師,在教堂、宮廷及市民活動中奏樂,共生8子,巴赫系其幼子。巴赫參加德國特有的乞童歌隊,每周3次穿過大街小巷以歌唱乞求佈施。8歲父母雙亡,寄居於兄長處,並從其兄學鍵盤樂器等,進步迅速。15歲起獨立謀生,往呂訥堡入中學,同時在教堂中擔任合唱隊女高音聲部歌手直至變聲。這兩年間,曾往漢堡聽著名管風琴傢J.A.賴因肯演奏,向北德管風琴藝術學習,並往策勒聽該地多由法國樂師組成的宮廷樂隊演奏,從而接觸法國音樂風格。巴赫的生活經歷和音樂創作活動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魏瑪-阿恩施塔特時期(1703~1707) 1703年4月,巴赫任魏瑪宮廷小提琴手,工資單中寫明是"仆役"。8月往阿恩施塔特任“新教堂”管風琴師。1705年冬,巴赫請假徒步赴呂貝克聽傑出的北德樂派管風琴傢D.佈克斯特胡德演奏,深受啟迪。數月後方返回阿恩施塔特。為此巴赫兩次受到宗教法庭的審訊,除因“擅自超假”外,還被譴責為“在眾贊歌中作出許多驚人的變奏,混入許多陌生的音響,使公眾為之驚惶失措”,並曾“把一個陌生的少女帶進教堂中演唱”,以及“在星期天講道時間上酒館”(據1706年2月22日及11月11日《宗教法庭記錄》)等等。巴赫憤而去職。
米爾豪森-魏瑪時期(1707~1717) 1707年6月巴赫任米爾豪森教堂管風琴師。同年與堂姐瑪麗婭·巴巴拉結婚。不久因與教堂監督發生矛盾,其演奏受到指責,乃離去。1708年7月任魏瑪宮廷管風琴師,兼為宮廷作宗教音樂。1714年起被任命為宮廷樂師,每月為宮廷創作新曲,因而作大量康塔塔。1717年秋,巴赫赴德累斯頓與法國哈普西科德演奏傢L.馬爾尚進行演奏比賽。臨賽前馬爾尚不辭而別,巴赫不賽而勝。魏瑪公爵與其侄發生爭執,巴赫傾向後者,致使公爵惱怒。巴赫要求離職不準,竟被公爵無理監禁4周,罪名是“由於其倔強,強行要求辭職”。巴赫在被監禁期間寫下《管風琴小曲集》。
克滕時期(1717~1723) 1717年8月巴赫任克滕宮廷樂長後的6、7年間,是巴赫一生中處境較為順利的年代,也是創作上(尤其在世俗性器樂創作上)豐收的年代。克滕公爵熱愛音樂,對巴赫非常器重,常在一起奏樂,一起旅行。他以國庫收入約1/30的經費作為其宮廷樂隊的開支。此期間巴赫寫下許多最重要的代表作:《平均律鋼琴曲集》上卷(1722)、《勃蘭登堡協奏曲》(1721~1723)、小提琴獨奏奏鳴曲(約1720)、大提琴獨奏奏鳴曲(約1720)、《創意曲》(1723)等。1720年7月他的妻子去世,1721年與安娜·瑪格達勒娜結婚。1720年11月旅行漢堡時,在賴因肯面前演奏管風琴,他以各種方式即興演奏眾贊歌變奏《在巴比倫河邊》達半小時以上,博得賴因肯的贊嘆。
萊比錫時期(1723~1750) 1724年,巴赫以其《約翰受難曲》作為接受考核的作品,去爭取萊比錫托馬斯教堂樂長這個頗具聲望的職位。萊比錫市議會和教堂認為該作品過於"戲劇化",但由於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隻得錄用巴赫。同時他還在尼可拉教堂供職,並兼事托馬斯教堂附屬學校的教學和演出工作。巴赫在萊比錫度過瞭他的後半生,寫下瞭265部宗教康塔塔、6部經文歌、5部彌撒曲、4部受難曲、3部清唱劇等宗教性樂曲,又創作瞭《平均律鋼琴曲集》下卷(1744)、《意大利協奏曲》(1735)、《戈爾德貝格變奏曲》(約1736)等世俗性樂曲。在萊比錫,他常與萊比錫市議會、教堂的主持人、教堂附屬學校的校長等發生沖突,也曾因反對教規、校規以及創作不符合教堂要求等,而屢遭譴責。巴赫並不屈從,曾上書議會和法庭進行申辨,致使市議會成員認為巴赫已屬“不可改正”,1730年決議予以減薪處分。1737年,他向德累斯頓的薩克森選侯奉獻作品,請求賜予“德累斯頓宮廷作曲傢”的頭銜,獲得批準。“宮廷作曲傢”的頭銜,有助於改善巴赫的處境。1747年,巴赫訪問波茨坦,為普魯士皇帝腓特烈演奏。返回萊比錫後,他又根據普皇的一個主題寫作瞭一部樂曲《音樂的奉獻》(1748)獻給普皇。最後,巴赫還寫作瞭一卷《賦格的藝術》(未完成)。由於他的體力日衰和雙目失明而就此擱筆,1750年7月28日逝世於萊比錫。
巴赫與宗教音樂 巴赫生活在18世紀上半葉封建落後、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終生在教堂和宮廷中供職,從未離開過德國。時代和環境的局限使他和當時德國大多數人士一樣,在思想、創作上打下深深的宗教烙印;但是這些並未妨礙巴赫作出偉大的創造。巴赫作為一位市民樂師,深刻地反映瞭18世紀上半葉德國市民階級中先進分子的精神面貌以及廣大德國人民的思想情感和願望。人文主義精神和德國的早期啟蒙思想(包括理性主義哲學),給予他深刻的影響。巴赫對當時的早期啟蒙哲學和數學有所接觸,曾讀過G.W.萊佈尼茲的《論智慧》。1747年加入L.C.米茨勒爾·馮·科洛夫創辦的“音樂科學協會”。巴赫音樂思維的高度邏輯性,結構的嚴密性,都和當時崇尚理性和數學的理性主義有所聯系。他對音樂科學的創造──十二平均律積極支持,並通過創作《平均律鋼琴曲集》加以應用和推廣,它不僅擴大瞭調域的應用、轉調的自由以及豐富瞭音樂語言和寫作手法,並且對於以音樂的科學理論取代音樂理論的神秘主義,也有重大貢獻。這種對理性、知識、科學的追求,正是對當時德國社會的愚昧、迷信和偏見的有力否定。巴赫的音樂富於哲理性,具有沉思冥想的性質和內在的思想情感。巴赫的音樂有其鮮明的個性,不論是悲劇性、戲劇性或各種生活風俗性的描繪還是豐富的內心刻劃,都達到瞭深切動人的境地。他作品中的不少悲劇性的樂章,深刻反映瞭當時德意志人民(尤其是市民階級)的苦難、掙紮、期望,體現出純樸、堅強的性格以及對光明、幸福的追求。盡管與此同時常有宗教思想情緒的流露,或向宗教尋求精神解脫的傾向,但始終與消極悲觀、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絕緣。堅實、宏大是巴赫音樂的基本性質。巴赫的音樂常在充滿壓抑的氣氛中,呈現出一種堅持不懈的倔強;哪怕充滿深切的悲痛,也包含有沉著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哪怕籠罩著一片深沉的黑暗,也不斷醞釀著力量,彷佛要突破桎梏、沖破黑暗,以致最後導向戲劇性的高潮和光輝的結束。在巴赫作的一些聲樂曲中,還有歌唱愛情、婚姻(《婚禮康塔塔》、《婚禮合唱曲》等)、吸煙(《煙草康塔塔》)、喝咖啡(《咖啡康塔塔》)等的生活內容。在許多器樂曲(包括各種舞曲)中,也體現瞭各種生動、活躍、輕松、甚至詼諧的形象。這些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瞭德國市民的生活,流露出對人世生活的熱愛和廣泛的樂趣。巴赫的音樂中更貫穿著一種充沛的生命力,常常具有江河直下、一瀉千裡的氣勢。他的一些代表作,如管風琴曲《d小調托卡塔與賦格》(1708~1717)、鋼琴曲《半音階幻想曲與賦格》(1720~1723)、《意大利協奏曲》(1735)、小提琴獨奏奏鳴曲《d小調恰空》(約1720)等,都具有宏大的氣魄和奔放不羈的性格,這正是新興的市民階級在先進思想的推動下,力圖掙脫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表現。巴赫經常忘乎所以地把教堂當成管風琴音樂會場,無拘無束地發揮其管風琴即興演奏的才華,常把宗教禮拜時用的《眾贊前奏曲》,通過各種變奏、加花(如《親愛的耶穌,我們在這裡》)和無比豐富而活躍的伴奏(如《歡樂吧,教徒們》,以及繁多的變音和富於色彩的和聲(如《在巴比倫河邊》),把原來眾贊歌曲調幾乎掩蓋瞭,使一般墨守教規和樂規的人“驚惶失措”。巴赫也常將他早已寫成的世俗樂段或曲調,直接引用到宗教作品中去,從而使宗教音樂中也滲透著世俗的因素。
巴赫與民間音樂 巴赫作為一位傑出的作曲傢,他的創作植根於德國民間傳統音樂之中,音樂語言極其豐富,並具有鮮明的個性。這首先表現在巴赫音樂(尤其是賦格)的主題和各個聲部的個性化上。不論是短小的動機或氣息寬廣的曲調,都有鮮明的輪廓和豐富的內涵,在反復的再現或變形中,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充分展示它的內涵,並且通過各種不同的和聲──對位的背景變換以及新的對比──變化因素的提供,使其在整個音流進程和升騰中顯得更加豐富而饒有新意。巴赫的音樂絕大部分以嚴謹的復調寫成。他的復調常結成為嚴密的音線之網,其中每根線條理清晰、脈絡鮮明,既有獨立的生命,而又各系整體結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每個聲部有它流暢的進行和不同的起迄、起伏,同時也基於明確的和聲功能性,從而使音樂織體的縱橫關系達到有機地完美結合的境地。巴赫的樂曲從整體結構上說尤為嚴謹而完整,往往具有宏大的幅度和寬廣的氣息,具有統一的廣闊發展而又內含豐富的對比變化,常令人聯想起同時代的巴羅克式建築:體積宏大、結構嚴密、比例對稱而均衡,同時也富於鮮明的對比和潛在的動力,以及華美、壯觀的裝飾。同樣巴赫音樂的形式結構也從不陷於呆板、凝滯,強勁的動力使它始終保持著生命的脈搏跳動和呼吸起伏。嚴密的佈局和邏輯的發展中,經常不乏自由幻想的因素和出其不意的新意,這使他在藝術構思中將嚴謹和自由這兩種對立的因素巧妙地統一起來。
中世紀以來,以民間藝人為支柱的德國民間音樂傳統,在人民中一直保持著。歷代充當民間藝人、城市吹鼓手或管風琴師的巴赫傢族的音樂傳統,也為巴赫所繼承。從幼年充當歌童起,巴赫即在接觸宗教音樂的同時,廣泛接觸民間音樂。德國民歌、民間器樂以及在民歌基礎上產生的新教眾贊歌是巴赫音樂語言素材的基礎。自馬丁·路德實行宗教改革以來,在德國各地設立教堂合唱隊的制度,世代延續不斷,這形成瞭德國(尤其是德國中部)所特有的一種音樂傳統。它對德國復調合唱、康塔塔和管風琴音樂的發展,都有重大作用。巴赫不僅繼承德國中部的音樂傳統,並對北德樂派和南德樂派的管風琴藝術和音樂風格等,也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繼承。在繼承本民族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巴赫富於創造性地廣泛吸取瞭外國音樂成就。自15、16世紀尼德蘭樂派以來高度發展的復調技術,17世紀以來以A.維瓦爾迪、A.科雷利等為代表的意大利器樂和聲樂藝術,以F.庫普蘭等為代表的法國哈普西科德音樂、室內樂和組曲的藝術成就等,都是巴赫學習的對象。
巴赫對後世的影響 巴赫的音樂創作標志著德意志民族音樂的開端,對後世音樂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德國屈服在外國的壓力和影響之下,經濟的落後、政治的分裂、精神文化的墮落,使得德國幾乎無民族意識可言。文化受法國影響的支配,宮廷操法語,學術界用的是拉丁文,主宰劇院和樂壇的是意大利人。當貴族統治階級在政治上日益依靠外國,在音樂上日益崇拜和模仿外國音樂的時候;當粉飾封建統治的宮廷音樂,死氣沉沉的宗教音樂,以及追求享樂的浮華、淺薄的樂風盛行的時候,巴赫的音樂堅持並發揚瞭質樸、堅實的德意志民族音樂的風格。當德意志民族的語言還未能統一的時候,巴赫的音樂卻已標志著德意志民族音樂語言的形成;當第1個使德國文學紮根於民族文化土壤的德國文學傢G.E.萊辛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巴赫的音樂卻已為德意志民族音樂奠定瞭基礎。這對於促進德意志統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識有著積極的歷史作用。盡管巴赫在世時,他的作品未能廣泛流傳,但經過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他的音樂日益發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自從1802年德國音樂學傢J.N.福克爾出版瞭第1部巴赫傳記以來,尤其是1829年F.門德爾松重新發掘、演出瞭巴赫的久被人遺忘瞭的《馬太受難曲》以來,巴赫的音樂在現實音樂生活和音樂教育、創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與日俱增。巴赫音樂思維的高度邏輯性和哲理性,其藝術-技術手法的嚴密、精巧,始終是學習作曲者的楷模。18世紀末葉的古典樂派大師W.A.莫紮特在其晚期創作中明顯地吸取瞭巴赫復調音樂的精神和手法。L.van貝多芬在音樂的邏輯性上更直接繼承和發揚瞭巴赫的成就。19世紀的浪漫主義音樂傢,如R.舒曼、F.門德爾松、F.F.肖邦等,也從巴赫的音樂中吸取靈感。20世紀各種不同傾向和流派的作曲傢,也分別從巴赫的音樂中獲得新的力量,如民族樂派的B.巴托克就把巴赫、貝多芬、C.德彪西列為他從中獲益最多的3位作曲傢。新古典主義的I.F.斯特拉文斯基,和新客觀派的P.欣德米特,更直接以巴赫的線條對位和巴羅克的音樂形式、手法作為其音樂寫作、乃至音樂風格的基礎。法國“六人團”的A.奧涅格也在“音樂建築”的嚴密性上以巴赫為楷模。綜上所述,巴赫及其音樂不僅是他以前音樂成就的集成者,更是他以後音樂發展的啟迪者。